
作为一个刚来 BIE 的 00 后实习编辑,在痛苦地写了一轮选题无疾而终后,主编给我转了三条每条长达五六个小时的纪录片网盘链接,我一点开,发现是三部本土纪录片,分别是从 2020 年到 2022 年的《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

 其中一部导演剪辑版总片长长达366分钟
其中一部导演剪辑版总片长长达366分钟
我很困惑,部分青年是什么青年?主编用一个问题回答了我的疑问,她问:“你是亚逼吗?”
我后来才知道,这三部《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也被叫做《北京亚逼三部曲》,大致记录了 2020-2022 年疫情到来之后北京 “部分” 青年们在各个 club 蹦迪、在各种地方瞎聊天的生活 。
我说,我不是亚逼,我只不过是染了头发。
主编又问,你觉得这选题好玩吗?也没其他好写的了,我点开 2021 年的那集看了十分钟,发现信息量就那么点,废镜头一大堆,我觉着还没我一学生剪得好。
比如说,跟拍一个人去医院开戒酒的药、几个人在什刹海的冰面滑来滑去然后开一瓶酒看夕阳,一群人喝醉了互相叫老公老婆,一个黄毛和另一个黄毛动不动就要展开一段漫长对话,基本大部分聊天既无逻辑也无意义:
比方说三人争论什么酒好喝,一人说他喜欢喝嘉士伯,并评论别人喝的麒麟也可以,后来,有些莫名其妙地,两个人开始因为乌苏好不好喝而对骂起来。
虽然莫名其妙,但看着看着愈发觉着这片子挺珍贵。虚焦、手持、长镜头,这种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形式恰恰和这些人迷茫的精神内核高度统一。我觉得这不是纪录片,应该叫“影像资料”,因为对素材丝毫不加拣选,而具有了一种社会学上的意义。但我唯一的问题是,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么事无巨细地拍下这群年轻人的生活 —— 或者粗暴一点说,谁没喝多过,谁没边抽烟边想过过自己前男/女友,谁没在其他人面前酒后表演过—— 这些值得被这么拍吗?在我一个00后的眼里,亚逼的意思变了
这三部片子的导演叫张帅,说实话,他拍的北京部分青年,其实挺符合外界对“亚逼”的刻板印象的:
他们大多在外表上有些自己的特点,打钉染发涂指甲油,经常出没于 club 舞池,要么有点情绪上的问题,要么与原生家庭有着不可和解之痛,还有一点很重要,亚逼得有点爱好,一些人喜欢跳舞文学电影,几乎所有人都喜欢音乐。两年前,张帅导演的三部曲才出了两部,BIE别的 曾写过一篇半影评半采访的文章,叫《亚逼是场梦,谁都可以做》,大致意思是本土青年面对的情况很严峻,于是催生出两种应对的态度,一是“内卷”,二是“亚”,在大厂拿高薪、在一线城市置业的“内卷”是社会的最强叙事,而那些或自愿或被迫离开这套叙事的年轻人就成了“亚逼”。只不过,原作者将亚逼划在了阶级光谱的特定范围里:也就是中产家的小孩。理由是“富人的小孩没必要亚”,他们生来自洽,而穷人的小孩没有消费主义和文化资本的加持,因此“亚不起来”。当时这篇文章掀起一阵小小的风波,对此,其中一个被拍摄者的回应大致是:哥们儿我初中毕业,21 岁拿到全国scratch dj冠军,之后自己创业,开过 2 家酒吧,5 家餐饮店,27 岁给京东华为设计年会和发布会的 ppt,我们的生活不只是狂欢和游荡,只是你看到的太少了。
而在另一篇被拍摄者的回应中,他表示 “亚逼” 是他们自嘲的词儿,在全民自称 “亚逼” 的时代,再被人称为 “亚逼” ,他们感觉到被冒犯了: 
我知道, “亚逼” 是一个粗暴的概括,这个词有趣的地方在于,“亚逼”的意义已经被扩充颠覆过多次,而沉淀得失去所指。如上图所说:“我们也自嘲自己是‘亚逼’……后来的后来,真正的亚逼开始以‘亚逼’自居,这词儿就变成了中性词……到这个时候,“亚逼”已经不再是我们嗤之以鼻的‘亚逼’了,开始全民‘亚逼’了,……当‘我们’被称之为‘亚逼’,我们感受到被冒犯了。” 所以,在我看来,能不能使用这词儿,不取决于这个词儿本身,而取决于使用它的人。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亚逼”这词儿有点像政治正确语境里的 “nigger”,用来互相确认就是惺惺相惜,用来区分异己就是粗暴凝视。“亚逼” 俩字一说出口,既是在评价别人,也邀请对方来评价你。你们彼此打量,想看看对方是不是“自己人”。也只有互相的认同感,能把 “逼” 这字儿天然的侮辱性,转化为一致对外的小小反骨。
也正是因为有上一回合的争议在前,我觉得自己在理解亚逼上反倒有了抓手,亚逼不喜欢被概括、被定义,因为这些动作一旦发生,就意味着将他们描述为“亚逼”的人没跟他们比肩而立,而是站在一个向下俯瞰的遥远的阵营里。据我一 00 后观察,“亚逼”这词儿的重点已经跟着时代转移了。前几年我们说亚,是说的一个人的“亚”,即个体的标新立异,或者说——“摇滚精神”,但现在的亚,指向的是一群人的“亚”。如果非要下个定义,我想“亚逼”是一种一群人的状态,你们互相确认,用彼此的认同感来指认自己。而不管是兴趣爱好、文化标签、消费主义,甚至是情绪问题或者原生家庭之痛,这些 “要素” 之所以会成为刻板印象里的 “亚逼” 标签,大概是因为它们都是能让人们迅速进入某一种共通的精神状态,并互相理解的几类特有 “当代感” 的通道。即便那些互相理解的时刻带着点言过其实的表演性又怎么样呢?我记得片中有一个情节,舞池中有一个女孩问张帅:你在拍一个人的时候,他肯定会有表演成分,你怎么保证你拍的是绝对真实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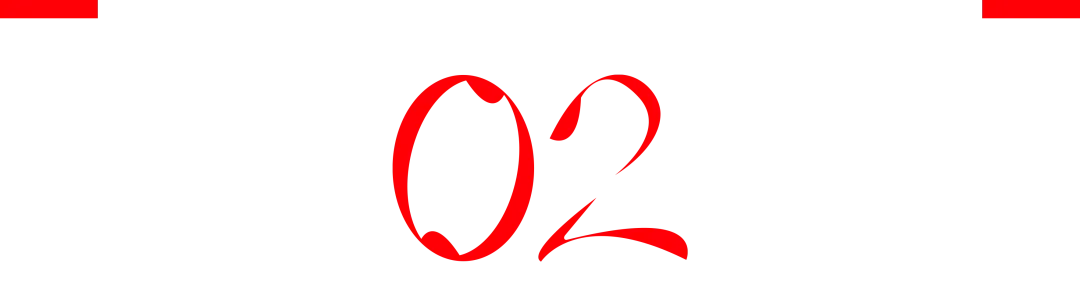 亚逼,是表现 “疫情” 这一主题的最好载体?
亚逼,是表现 “疫情” 这一主题的最好载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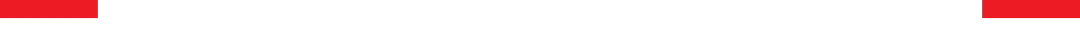 好了,现在我自认为初步厘清了“亚逼”一词的意涵,就又回到了那个最初的问题:这三部纪录片时长总计 19 个小时,为何非得如此事无巨细地记录下这帮年轻人看似没有主题和情节的生活?在张帅看来,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按照一些学院派的拍法,纪录片里的人物得有内部反差和外部目的,内部反差让人物好看,外部目的让人物有行动,有了行动整个片子才有结构。从片中展现的部分来看,没有一个人有明确目的,也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可以称得上戏剧行动的行为,大家都处在一种有点“无意识”的状态中。甚至,我觉得张帅导演本人也没什么意识,并不试图用素材组成叙事,而是把生活本身放上剪辑台上,没剪几刀就导出成片了。据张帅本人说,他就是喜欢这种巨长的片子(他特喜欢王兵和赫尔佐格),喜欢带你进入一段旅途的感觉。冬天, 什刹海冻得跟冰砖似的,女孩 GG 和大凉山来的美姑就那么坐在岸边,啥也不干,GG 说你下去的话冰可能会崩裂,美姑说是的,我有你两倍重,肯定能裂。然后俩人又一块儿讨论昨晚谁喝醉了、谁把谁的衣服穿错了穿走了,是否认识哪个共友。美姑给 GG 递烟,俩人一块儿抽烟,GG 揶揄他,你还会发烟了,能抽上美姑而发的烟,GG 很开心。夕阳西下,美姑拿出手机拍了一下。而后又是抽烟、干杯、喝、抽烟。无限循环。就是这样一部漫无目的的片子,被张帅赋予了一种“社会学上的意义”,他解释说,自己本来是想拍疫情的,而且就想拍疫情之下普通人的生活。这群被看作是“亚逼”的北京年轻人是他最容易接近到的拍摄对象。“从中国有这个独立纪录片以来,大家的选题似乎要么是边缘群体,要么就是那种很高的东西,其实中间是断层的,就是没有人去记录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张帅的选择在我看来无可厚非,也许刻板印象里的“亚逼”,确实是最适合展现疫情的拍摄对象 —— 他们具有敏感的神经,和无处宣泄但一触即发的能量。这种离经叛道的精神,让他们在口罩期也总能找到某些缝隙开派对或狂欢。 在《2021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中,蛋仔把大块五颜六色的塑料布剪掉了很多孔,布置了酒吧的天花板,将废墟和末日的感觉带进了酒吧。站在涂鸦前面,天空被远处的红光点亮,她张开手臂,说,看,像不像世界末日。
好了,现在我自认为初步厘清了“亚逼”一词的意涵,就又回到了那个最初的问题:这三部纪录片时长总计 19 个小时,为何非得如此事无巨细地记录下这帮年轻人看似没有主题和情节的生活?在张帅看来,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按照一些学院派的拍法,纪录片里的人物得有内部反差和外部目的,内部反差让人物好看,外部目的让人物有行动,有了行动整个片子才有结构。从片中展现的部分来看,没有一个人有明确目的,也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可以称得上戏剧行动的行为,大家都处在一种有点“无意识”的状态中。甚至,我觉得张帅导演本人也没什么意识,并不试图用素材组成叙事,而是把生活本身放上剪辑台上,没剪几刀就导出成片了。据张帅本人说,他就是喜欢这种巨长的片子(他特喜欢王兵和赫尔佐格),喜欢带你进入一段旅途的感觉。冬天, 什刹海冻得跟冰砖似的,女孩 GG 和大凉山来的美姑就那么坐在岸边,啥也不干,GG 说你下去的话冰可能会崩裂,美姑说是的,我有你两倍重,肯定能裂。然后俩人又一块儿讨论昨晚谁喝醉了、谁把谁的衣服穿错了穿走了,是否认识哪个共友。美姑给 GG 递烟,俩人一块儿抽烟,GG 揶揄他,你还会发烟了,能抽上美姑而发的烟,GG 很开心。夕阳西下,美姑拿出手机拍了一下。而后又是抽烟、干杯、喝、抽烟。无限循环。就是这样一部漫无目的的片子,被张帅赋予了一种“社会学上的意义”,他解释说,自己本来是想拍疫情的,而且就想拍疫情之下普通人的生活。这群被看作是“亚逼”的北京年轻人是他最容易接近到的拍摄对象。“从中国有这个独立纪录片以来,大家的选题似乎要么是边缘群体,要么就是那种很高的东西,其实中间是断层的,就是没有人去记录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张帅的选择在我看来无可厚非,也许刻板印象里的“亚逼”,确实是最适合展现疫情的拍摄对象 —— 他们具有敏感的神经,和无处宣泄但一触即发的能量。这种离经叛道的精神,让他们在口罩期也总能找到某些缝隙开派对或狂欢。 在《2021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中,蛋仔把大块五颜六色的塑料布剪掉了很多孔,布置了酒吧的天花板,将废墟和末日的感觉带进了酒吧。站在涂鸦前面,天空被远处的红光点亮,她张开手臂,说,看,像不像世界末日。
在餐厅里,醉了的哥们端起酒杯,一字一句慢吞吞地说,咱们也没有不开心,咱们也没有矛盾,咱们就玩游戏好不好。 这个哥们是全片中只出现过一次的人,他看起来最不像“亚逼”——没有彩色头发,也没有钉子、纹身,整个人打理得和大厂上班的年轻人没什么区别。他一字一顿地说,我发疯,但我能赚钱。当被问到,你对自己的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的时候,他吞咽、眨眼、又挑了挑眉毛:“说真心话吗?说实话吗?” 他看向天花板又转过来看向朋友, “因为要是你这么问的话,说实话,我会去死。”
张帅跟我们一再厘清,他想拍的并非“亚逼”,而是那段特殊时期本身。在记忆中,大部分关于口罩时期的影像资料都是跟医院、隔离点、做核酸等内容直接相关的,然而,囿于只能接触和拍摄到这些年轻人的客观因素,张帅缔造了另一种疫情影像:这里面没有核酸和封控,但年轻人的敏感、鲜活和不安分,让那段特殊时期作用于普通人的心灵震荡,被毫不削弱地呈现了出来。那些胡言乱语和夸张行为,对抱团取暖的强烈渴望,都被这一件事情强化了。有一个镜头我印象挺深刻,一群凌晨上街的亚逼们对着镜头说,张导,记得给我们 p 个口罩啊。 所以,这《北京亚逼三部曲》虽然看着都挺散漫,但实际上有一条情绪变化上的暗线:“19 年底开始疫情之后,到了 20 年夏天,其实大家已经觉得这事大概就差不多过了吧,所以还沉浸在 19 年整体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美好幻想中,就觉得疫情这么几个月过了,20 年的夏天之后再继续辉煌嘛,所以那个时候有点像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刚过去的样子。然后到了再下一部,大家就发现这事不对了,怎么越来越严重了。22 年的主题很明确,就是那种末日狂欢的感觉,面对未知的未来,大家就破罐子破摔了,那种绝望的狂欢是我想尽力去展现的。” 用张帅的话说,“这个片子的社会学意义,就是好像大家都忘了,或者说装作忘了,好像只有我记得这件事一样。这个影片也是为了记住,可能你在未来,再回想这三年的事的时候,你不仅能看到主流叙事下的关于疫情的记忆,也能看到普通人的记忆。”我想起 2021 年那一部中,那些意识流对话中的一句,似乎解决了一切喝啊蹦啊看夕阳啊其实也就是那么呆着啥也不干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喝酒还能干啥。”聊到这里,我也跟张帅说了说我对 “亚逼” 的看法,我说感觉在这个片子里,“亚逼”比起文化身份上的标签,更是一种状态,而疫情这事儿作为一种集体性创伤,又让 “亚逼” 这种状态特别成立,好像在这种状态里,你会更温暖、更开心、更有安全感。我问张帅对我的理解怎么看,他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其实有一个被拍摄者,后来回看片子觉得挺不能理解当时的自己,她说:“我当时怎么疯成那样”。
 谁也别说谁,都亚
谁也别说谁,都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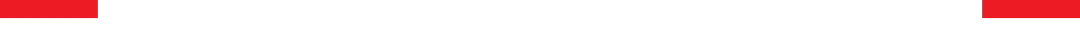
《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这片子的命运,其实挺跌宕起伏的。张帅至今也没找到能发行的渠道,片子在北京亚逼的百度网盘里流传,只要你经常去那几个 club 跳舞,你和你的朋友都大概率在这片子里现身过。谁能不喜欢看有个人用拍奥德赛史诗的劲头记录下身边朋友酒后犯傻的实况呢?但是张帅实在不能满意片子就这么止步于此,“自己发个朋友圈,认识的朋友点赞然后看看其实有点太可惜了。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原因让张帅挺不甘心的,就是这样一部制作粗糙的、技术问题一大堆、不符合传统纪录片结构的片子,入围过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张帅说那时候他只是乱投投到了平遥,结果平遥选片人告诉他,这个播不了,但我可以帮你投到国外的影节影展,比如鹿特丹电影节。 那是张帅第一次听说这个电影节,他就说行吧,我就委屈委屈吧这样。结果入围之后他一搜才发现这节这么厉害。“那时候我就有点膨胀,我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简直,我是天才。”我问那你现在还这样觉得吗?他脸上的光慢慢黯淡下来,说他现在不这样觉得了,现在认识到自己当时拍的太业余了太粗糙了,且后来才知道那一年刚好鹿特丹改组,选片人就喜欢他那种很怪的东西,一系列的巧合才让他入围。  得知自己入围后,张帅的第一反应是去查一下这个电影节是不是真的 聊到这儿,张帅提议我们出去抽根烟,主编接过来他的打火机点着后,张帅立马警惕地说,“火机还我。” 主编笑了,张帅挠头,“因为我经历过那种,每天只能用煤气灶打火的那个阶段,之后就对这个特别警惕,不要想顺走我的火机。” 从机械与电子工程学系毕业后,热爱电影的张帅以执行导演或者剪辑的身份参与一些广告和时尚行业物料视频的拍摄,他说,出于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失望,自己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电影行业;而这三部纪录片则是在一种迷茫中辞了工作,用花呗买了相机拍的。张帅曾在 Fruityspace 放过他的纪录片,从下午1点播到晚上8、9点他自认为自己是搞影视的,但因为他搞的东西太小众,好像搞影视的也不太认同他,他挠头、有些窘迫地跟我们说,“我发现我好像把自己的职业道路越走越窄了。” 我问导演,那现在在干嘛呢?张帅说现在在好好工作,认真做自己的剧情片。他说也想让自己再变聪明一点,他开始戒酒了,学会和电影行业里的人接触,发一些可爱的表情。就是在这时,我突然觉得张帅也挺“亚”,我紧接着反思了一下自己这个稍纵即逝的念头,意识到我也是学电影相关专业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能理解他。我想,之前主编问我“亚不亚”时,我之所以说“不亚”大概就是出于叛逆,没有亚逼愿意在审视的目光中承认自己亚。但如果我们真正互相理解过,我不介意用“亚”这个字,来连通我们不主流的生活。
得知自己入围后,张帅的第一反应是去查一下这个电影节是不是真的 聊到这儿,张帅提议我们出去抽根烟,主编接过来他的打火机点着后,张帅立马警惕地说,“火机还我。” 主编笑了,张帅挠头,“因为我经历过那种,每天只能用煤气灶打火的那个阶段,之后就对这个特别警惕,不要想顺走我的火机。” 从机械与电子工程学系毕业后,热爱电影的张帅以执行导演或者剪辑的身份参与一些广告和时尚行业物料视频的拍摄,他说,出于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失望,自己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电影行业;而这三部纪录片则是在一种迷茫中辞了工作,用花呗买了相机拍的。张帅曾在 Fruityspace 放过他的纪录片,从下午1点播到晚上8、9点他自认为自己是搞影视的,但因为他搞的东西太小众,好像搞影视的也不太认同他,他挠头、有些窘迫地跟我们说,“我发现我好像把自己的职业道路越走越窄了。” 我问导演,那现在在干嘛呢?张帅说现在在好好工作,认真做自己的剧情片。他说也想让自己再变聪明一点,他开始戒酒了,学会和电影行业里的人接触,发一些可爱的表情。就是在这时,我突然觉得张帅也挺“亚”,我紧接着反思了一下自己这个稍纵即逝的念头,意识到我也是学电影相关专业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能理解他。我想,之前主编问我“亚不亚”时,我之所以说“不亚”大概就是出于叛逆,没有亚逼愿意在审视的目光中承认自己亚。但如果我们真正互相理解过,我不介意用“亚”这个字,来连通我们不主流的生活。应张帅强烈要求,我们放上了《2022年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的预告片,如果你想看完整版,请在 YouTube 或 B站 上搜索“2022年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观看全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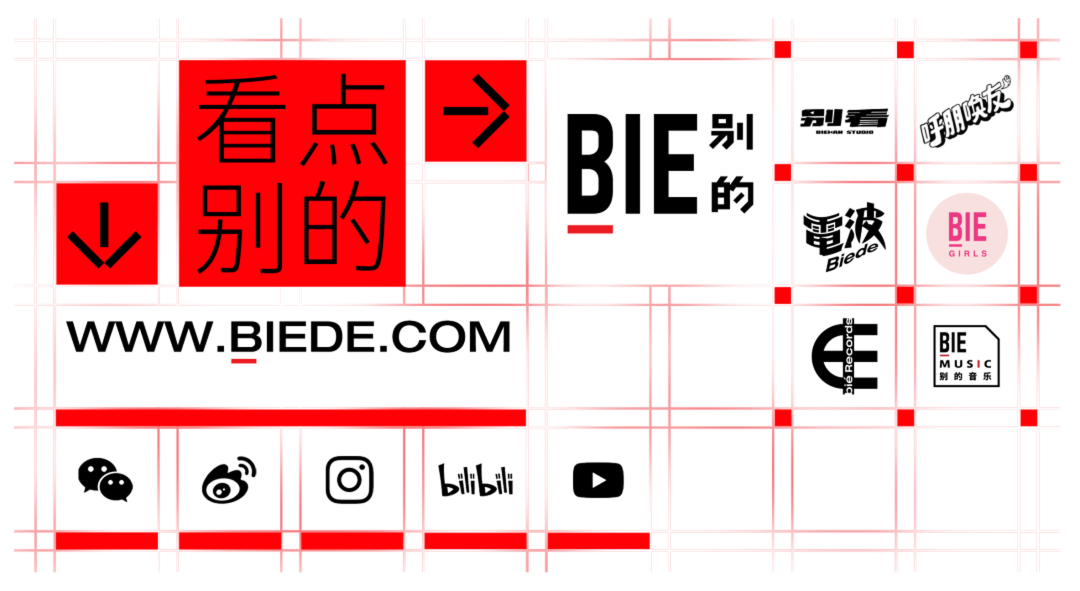
其中一部导演剪辑版总片长长达366分钟
谁也别说谁,都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