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于北京时间27日凌晨1:30正式开幕。有别于过往在体育馆举办的传统,这届开幕式沿塞纳河两岸举行,超过30万名观众在塞纳河畔观看仪式。
在开幕式中,十座镀金雕像从塞纳河畔缓缓升起,该章节旨在颂扬法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代表,被命名为“Sororité”(女性友谊)。十位女性的职业各异,有起草女性宣言的政治家,有创办女子运动会的优秀运动员,有维护女性合法权益的律师,有为女性权益而奋斗的作家,有倡导不同种族女性平权的记者,有首位实现环球航行的女探险家,等等。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其中一位杰出女性——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女性政治家西蒙娜·韦伊的人生。西蒙娜·韦伊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是赋予法国女性堕胎权的立法者,也是致力于实现欧洲和解与团结的政治家。在韦伊的自述《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杰出女性坚韧不拔的灵魂。而在这强有力的性格背后,是惨痛的集中营遭遇。虽然我们无法真正感同身受,但是韦伊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带着伤痛前进的方法:不要停下做事情的脚步,并且相信自己可以拥有正常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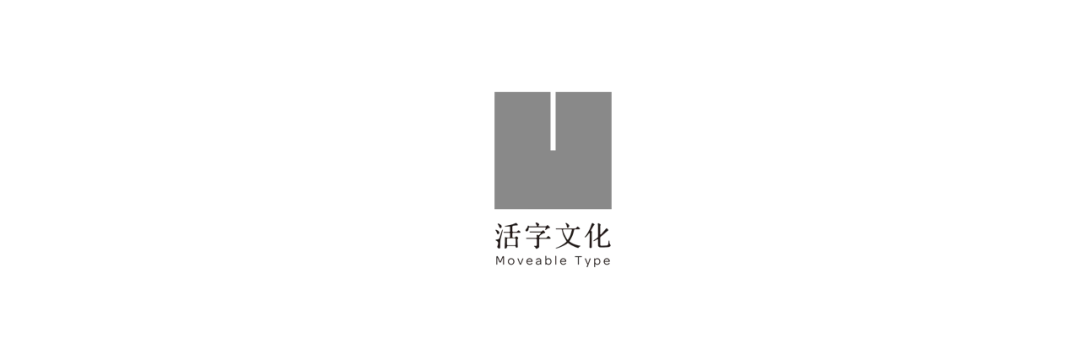

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1927.7.13-2017.6.30)生于法国尼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法国卫生部前部长;欧洲议会前议长,也是第一位女性议长;法国宪法委员会前成员。1998年获得英国政府的荣誉勋章(DBE)。2008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死后葬入法国先贤祠,她是历史上第五位被安葬在先贤祠的女性。
1944年4月,西蒙娜·韦伊和家人被押往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在集中营里,党卫军在新来的囚徒的手臂上文上编号,并将处于惊惧之中的人们送往一间间砖砌的长条棚屋。

劳役期间,面对那些担心亲属命运犯人的问询,卡波们(Kapo,与纳粹合作的囚犯,他们在纳粹集中营中担任领导或行政职务)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之前和你们在一起的那些人......看看那些烟囱吧,他们都进了毒气室,尸体已被焚化。剩下的就是这些灰了。”西蒙娜在自述《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中讲道“那股持续不散的味道。近在咫尺,挥之不去......”

在奥斯维辛,时年17岁的韦伊,看到了人可以非人到何种程度。直至西蒙娜·韦伊步入老年,某种特殊的味道,一丝寒冷,哪怕一个幻象都能让她产生一种被她称为闪回的东西,勾起模糊而残酷的记忆。这种情况总是来得猝不及防。“有时,一个起初看起来非常正面,甚至是幸福的画面都可能会引发焦虑。哪怕看着一群孩子都能把我带回大屠杀的年代”。
西蒙娜·韦伊在集中营总共待了十三个月,而多的是比她待得更久的人。韦伊的母亲在1945年解放前夕死于伤寒,父亲和哥哥被送往立陶宛后再也没能回来。韦伊和妹妹活了下来,但妹妹在战后不久就死于车祸。在西蒙娜·韦伊看来,没有什么能和这段经历相提并论。“在我们能读到的和人们能写出来的东西与那种绝对的恐怖相比,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在自述《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里,韦伊说。

战后,韦伊带着无法抹去的记忆创伤前进,她在巴黎政治学院学习法律和政治学,之后进入政界。1954年,她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了一名法官,并处理了阿尔及利亚的监狱问题。
1974年11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开启了讨论关于流产的计划法案,时任卫生部部长的西蒙娜·韦伊在国民议会发表45分钟强有力的讲话,随后在讲台上连续3天,力辩以男人为主、敌视堕胎的数百位议员,连同聚集在议会外抗议杀生的神甫和不明真相的妇女,要他们正视每年三十万例非法堕胎的现实,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的羞辱和创伤,最终推动议会在29日通过了“韦伊法”——《自愿终止妊娠法》,使法国成为第一个堕胎合法化的主要的天主教国家,对现代法国的妇女解放和世俗主义意义重大。
以下为西蒙娜·韦伊的自述,节选自《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

1974年,德斯坦在总统竞选时提出要让自愿终止妊娠合法化。当选之后,他便着手促进这个计划的实现。在以希拉克为首的内阁中,让·勒卡尼埃(Jean Lecanuet)任司法部部长,我是卫生部部长。在促进自愿终止妊娠合法化这件事上,德斯坦更倾向从公共卫生而非司法的角度切入。指针已向我倾斜。不仅如此,总统还认为这样一个计划由一个女性来辩护更容易。而且,他在这件事上非常坚定,毫不犹豫地推行这一计划。他的内政部长,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Michel Poniatowski)之前一直在提醒他:非法人流已呈泛滥之势并对日常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当时的总统多数派里包含有中间派、戴高乐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党,这些人中反对这一计划的不在少数。就连总理雅克·希拉克一开始也并不看好这一议案。他觉得这不过是总统的突发奇想。由于充分了解该议案在其阵营中是多么的不受欢迎,他不是很明白我为什么要如此坚持。可当政府做出决定后,该议案就变得势在必行了,必须要通过立法投票。之后,希拉克开始给予了我全方位的支持。首先,是精神支持。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其次,是政治支持。当需要对法案进行一些修正,尤其是那些与自愿终止妊娠相关的修正时——这非常重要——他总会站在我这边。在议案投票结束后,我觉得周边,无论是我身边还是更为上层的政治圈,尤其是总统多数派的一些成员,对我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非立刻出现,因为大部分人认为我的声望肯定是昙花一现。很多人说:“人们是注意到她了,可她始终是个新人,这种声望维持不了几个月。她有那么重的文书工作要做,最终一定会以失败告终。”那时,很少有女性会在政治上冒险。可出人意料的是,我的声望不但没有减弱,还得到了民调的证实,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专家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高的声望可以延续这么久。哪怕之后我不再涉足法国政坛,我的民望依旧。这无疑让我所属的政治阵营产生了某种不快。一些人私下会说:“无论如何,西蒙娜·韦伊是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笨嘴葫芦,无知透顶。她就是傻人有傻福。她就会煽情,知道怎么在民众面前哭,这是她唯一会做的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已经对一些事情习以为常了:我在左派中的形象远比在一些保守的右派中要好得多。在后者这个圈子里,经常有男性对我说:“我的夫人非常崇拜你!”原话就是如此。好像只有女人可以欣赏其他女人一样......1977—1978年间,很多人担心自愿终止妊娠法案的成功会让我一举登顶。人们担心我会因此生出不该有的野心,危及我们这一阵营中的其他候选人。1979年,当欧洲议会首次举行普选时,德斯坦让我代表“法国民主联盟”政党(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简称UDF) 参选。当我成为欧洲议会主席,离开法国政坛后,有些人如释重负。后来,一些人,或者说一些女性,总试图让我回归法国政坛,甚至提出让我参选法国总统。这种提议通常都来自女性,她们总说不能让事情再这样下去了,必须要继续为女性主义抗争。直至今日,每当有选举,总有人给我写信:“法国需要您。”确实,在198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我领导的右翼联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我们取得了43%的选票,并成功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绝对多数。这无疑是一次完胜。不过,法国右派却极力降低这次胜利的影响。我又一次意识到自己踩到了一些天然盟友的痛点。他们生怕我会以总统宝座为目标,强势回归法国政坛。确实,在法国机构里,一切都围着总统的位置转,好像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政治目标了。当时,若是我参加了某个政党,或是积极参与某些活动,抑或有什么很重要的责任需要承担,我或许会投身这场战斗,哪怕就是为了让一个女人成为总统候选人似乎也是个不错的理由。可我完全不想加入任何一个政党。这与我本性不符。要做出太大的牺牲。我承认,我的政治生涯确实是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如有神助。我选择了独立。因为我从不觉得自己能够服从某个政党的纪律,或是成为一个好的斗士。我太爱提意见了。当我进入一个组织,我必然会提一些意见......哪怕会让人震惊,甚至引起误解。我曾经属于右翼联盟,可很多左派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可若我属于左派联盟,右派人士大约也会说:“为什么她不加入我们?”我学会了如何在边缘生存,然后就一直处于这种状态。这很符合我的本性。在我提出某个议案时,我总会设想自己是反对派的一员,然后将自己的议案批得体无完肤。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些攻击我的言论实在是太没有水平了。我自己的批评比他们的要好得多。哪怕是我自己提出的议案,我也很快就会提出抗议。反正,这些议案最后也从来不曾像我设想的那样。不过,我也承认,当有人批评我时,哪怕是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或仅仅就是一些建议,我的第一个反应也大多会是“不”。更准确一点,我会说:“不,不过我会看看。”这个“不”其实是一种不信任的否定。我害怕被人左右,失去控制权。我的心态很难解释:怀疑是我的天性,但是在一些问题上,我又极为坚持。我经常听人说:“简直没法和你商量!”一些时刻被我挂在心上的事情,这五十多年来已经被我反复思量多次。怀疑它们会让我极为痛苦。我也经历过一些激烈的冲突,包括和我同阵营的一些人。在自愿终止妊娠议案的辩论中,我看到不少自己非常喜欢和尊敬的人突然变得声色俱厉。他们对我口诛笔伐,说出来的话远超我的想象。要是这些批评来自一个与我而言毫不重要,毫不相干的人,我完全不会有什么感觉。可若是那些我十分尊敬的人这么说我,我就会被伤得很深。米歇尔·德勃雷就是个例子。出于人口学的考量,他非常反对自愿终止妊娠的议案。他认为这将对法国的生育率造成极大的影响。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但他对我本人和观点始终保持尊敬。他的语气和用词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一些与我相识或不相识的公众人物则对我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攻击。这些人中不仅有我的政治同盟,也有一些我十分尊敬的人,我们也曾一度交好。他们用极其粗暴的语言攻击我。让我觉得哪怕议案的发起者是个男人,辩论都不会这么艰难。话说回来,男人恐怕很难让这部法案得以顺利通过。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和丈夫安东尼(Antoine)的棺木进入先贤祠,2018年7月1日,巴黎 ®REUTERS/Philippe Wojazer除此之外,还有排犹主义。无论是在堕胎法案的辩论阶段,还是投票阶段,甚至是法案通过后的那几年,我都曾收到侮辱性的信件。打开信件碰到一些侮辱性的语言或恶劣的图画可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这些信件我保存了大部分。可惜,没能全部留存下来。我的秘书们最后向我坦诚,一些信件的内容实在过于可怕,她们看完就马上撕掉了。还有很多信件是在我离开政府部门之后才送达。我本应更为警惕,让部里帮我保管这些信件并对其进行分类。大量此类信件都被销毁了。我保留了很多包含排犹主义内容的信件。这些信上都标有反万字符和辱骂之语。自从提出自愿终止妊娠法案之后,这种信件就未曾断绝。不过,我要强调的是,不是所有反对这一法案的人都是排犹主义者,这两者并不能混为一谈。不过,确实有很多排犹主义者借着反对法案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提出自愿终止妊娠法案之后,我就遭到了“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的猛烈抨击。当时他们还处于政坛的边缘,宣扬起排犹主义来也比现在更加露骨大胆地多。我对这些攻击毫不在意。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当对手已经无可救药且令人反胃时,他也就无法触及你本人。让人担忧的是,有那么多的人被这个政党牵着鼻子走,为他们投票,甚至搞不清楚他们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后来,排犹主义言论也会出现在和我相关的其他争论之中。1993年,欧洲议会对是否允许在动物身上试验化妆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作为欧洲议会的前议长和现任议员,我收到了成千上万封要求禁止一切动物实验的请愿书。那时最重要的动物保护协会都使用动物大屠杀,后来甚至用上了动物灭绝这种词汇。他们开始与一些曾受过纳粹迫害的欧洲议员接触,并直接联系上了我。他们是特意找的我,因为在这种背景下,我似乎自带环保的色彩,拥有一种不会因纷杂政见而却步的同情心。至于带有排犹主义色彩的人身攻击,这些年来已经少了很多。也许是因为排犹主义已转向他途,以其他的形式呈现;也或许是因为我的敌人们不敢继续从这种角度来攻击我。好在,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今天,关于自愿终止妊娠法的讨论已被收入学校的教材。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历史。有时,当有人找我签名时,我会和一些家庭面对面。年轻人看着我尚在人世甚为惊讶。对于他们来说,我已经是个历史人物,一个过去的人物......另外,发表人物传记,做人物访谈,这不一般都是等人物盖棺定论之后才会做的事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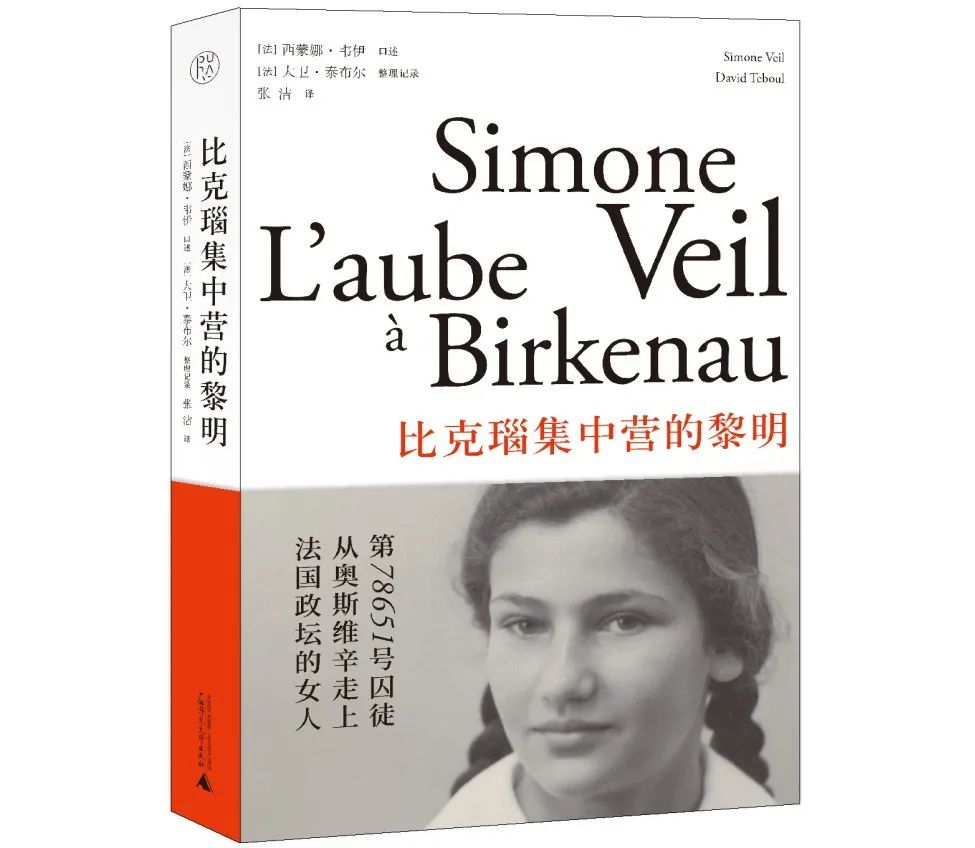 [法] 西蒙娜·韦伊 口述 [法] 大卫·泰布尔 整理 张洁 译
活字文化 策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6月 |
|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西蒙娜•韦伊纪录片的导演叙述,第二部分为西蒙娜·韦伊自述,第三部分为西蒙娜·韦伊与朋友们的谈话。其间配有纪录片剧照与西蒙娜•韦伊儿时的照片,共计60幅。西蒙娜·韦伊曾经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进入集中营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经历了摧毁人性的暴力和骨肉分离的悲痛,看过了人可以非人到什么程度,韦伊的心灵被蒙上永久的阴影,一如手臂上的文身。 在本书中,韦伊全面讲述了集中营前后的经历,惨痛的遭遇我们无法真正感同身受,但是韦伊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带着伤痛前进的方法:不要停下做事情的脚步,并且相信自己可以拥有正常的生活。除此以外,奥斯维辛幸存者的视角也是馈赠给读者珍贵的礼物,当她谈起自己的遭遇、挣扎和努力时,是在用个人的经历书写一段历史,云淡风轻之下有一股深邃而超拔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助她走上政坛,也是这股力量打开了女性被压抑的种种可能性。 |
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