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你会记住一个中年女人给自己改写的新名字:雨素。
范雨素,作家,育儿嫂,家政工。
2017 年,你曾经被她那篇《我是范雨素》刷屏,“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7 年后,我们发现她其实还有一个藏起来的故事,关于名字,做梦,还有白裙子。
她生在湖北农村,原名范菊人,她不甘心她的名字,就像她不甘心她的命运。
她在 12 岁觉醒了一个梦:一个白裙少女在雨里行走。于是她给自己改名叫「雨素」,雨是濛濛细雨的雨,素是白裙子的素。
但直到她结婚、离婚、生了两个孩子,从少女走到中年,雨素这个美丽的名字,从没被人叫过。白裙子因为干活不耐脏,从没穿过。
出来打工摆摊,别人叫她湖北佬。后来做保姆,大家对保姆的统一称谓,都是阿姨。
她对此并无不甘,“大多数人走在路上,不会被看上第二眼。大多数人的名字,一生都不被人知道。”
见面那天,我们聊到她尘封的白裙子,她突然跃跃欲试,要不回家换上?
于是,我们记录下了范雨素人生第一次穿上白裙子的样子。

她搭配了银色的高跟鞋,海星形状的发卡,去温榆河边散步。
那天的天气格外好,河水被映照成蓝色。皮村时时刻刻都有飞机驶过,像她描述的梦一样轰隆作响:要改名,要离家,要写作。
她脸上时常会露出做梦一般的神情,她一直是个有梦的人。

下面是雨素讲的故事。
这也是「那些给自己改名改命的女性」系列第一期。如果你也曾改写自己的名字,欢迎告诉我们。名字的力量,永远掌握在拥有它的人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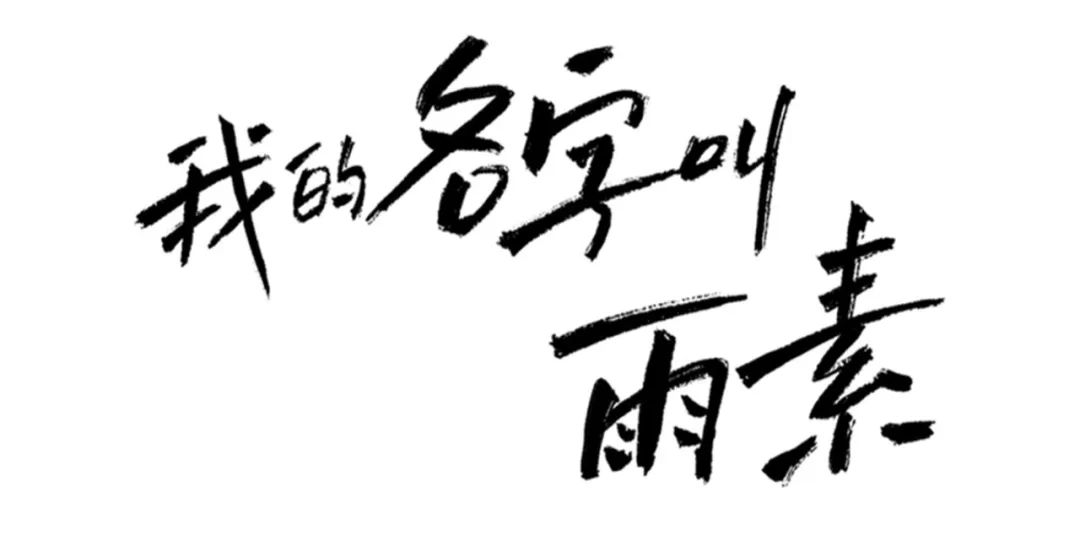
我姓范,我的名字叫雨素。这是我在混沌的前半生里,亲手给自己起的名字。
1973 年,我在秋天出生,生在湖北襄阳的一个农村,跟大诗人孟浩然同县。但很显然,我的父母在起名这件事上不具备太多诗意,我爸说我是来自海里的生命,所以应该叫范浪。哪家女孩叫这名字啊?我妈马上就给否定了。那个季节开菊花,她就给我起名叫范菊人,意思是在秋天成了人形。我还是一点都不喜欢。农村女孩的名字都跟花花草草有关,什么梅花、金桂,太普通了,没意思。
“我是最右边脸最大的那个。
我的童年,我妈忙得从来不管我,我上学,放牛,给猪割草,在六七岁时,学会了自己看小说。看到十二岁,我命中注定一般地,翻开了琼瑶阿姨的《烟雨濛濛》。《烟雨濛濛》是那年最畅销的书,就好像我们今年的畅销书是李娟的《我的阿勒泰》一样。我当时看到书名,脑子里就像过电一样,迅速闪过一个画面:细雨里面,有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子。
农村下雨很烦的,都是泥巴路。也不会有谁闲到穿白裙子到处走,干活一点都不耐脏。那一刻起,我就决定送自己一个新名字:范雨素。雨,就是濛濛细雨。素,就是白色。在我们那个年代,改名不像现在一样麻烦。16 岁办身份证,一切信息都是手写,我直接就把名字改了,什么流程都不要。我告诉自己,只要保住这个名字,就能保住自己对梦的向往。

可惜的是,雨素这么美的名字,在我的前半生,其实根本没有人叫。家里没人关心我改不改名。都被生活磨得麻木了,糟心的事一堆,谁会有心情提呢?20岁,我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来到了北京,结果比在农村过得更苦,日子潦草,像戴着眼罩的毛驴似的,没有规划。我在饭馆做过服务员,在潘家园倒卖过二手书,在天桥摆摊。
摆摊时大家都用你是哪里人叫你,我是湖北人,就叫我湖北佬,年轻叫小湖北,老了叫老湖北。
后来我稀里糊涂把自己嫁了,遭遇家暴,六年后离婚,独自带两个孩子。我在最该看护自己女儿的时候做了育儿嫂,看护别人的孩子。雇主的小婴儿睡觉不踏实,我半夜起来喂奶粉,哄她入睡。这时,我就想起我在皮村的两个女儿。晚上,没有妈妈陪着睡觉,她俩会做噩梦吗?会哭吗?想着想着,我也哭了。还好是半夜三更,没人看见。人都有惰性,我压根不是什么生下来就勤劳善良的人,那不都是逼的吗?有了孩子,就不得不坚韧。你就像遵循动物的本能,没有时间去抑郁,没有时间去想意义。
我打工做的都是很底层的工作,干的是最下力气的活,我们那些做育儿嫂的朋友,都说自己是隐身人。别人看不到你,你也懒得看别人。
大多数人走在路上,不会被看上第二眼。大多数人的名字,一生都没被人叫过。
来采访我的记者说,2017年,一夜之间,朋友圈到处都是我的名字。传阅我的人生,传阅我这个人,传阅我文章开篇那一句话:“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那年我已经 44 岁了,以我当年的阅历,我以为就是写篇文章,人家给点稿费改善生活,不懂什么是流量,也不知道什么叫流量变现,一点妄想都没有。阅读量一万一万地往上涨,后面的采访我都躲了,借口说去了附近深山的古庙。别人都说我耽误了发大财,耽误就耽误了,我耽误了也没饿着,可能人太穷了就没有虚荣心了,就觉得火是天上掉的东西,应付不了的时候就不应付。我只依稀觉得,雨素这个名字好像第一次派上了用场,我这个名字,就好像我下决心给自己买了一个名贵的皮包,放在那里藏了很多年,从来没用过,现在终于有机会背了出来。
你说,出名出名,不就是名字被别人知道了吗?
那篇文章其实本来是写我妈妈的,叫《我的农民母亲》。
我妈的名字叫先芝,是灵芝的意思。但在她人生的前半段,只有一个贱名,叫小狗。农村习惯起个贱名好养活,村里光是叫狗的同龄孩子有两三个。为了好区分,人家看我妈头发又黑又亮又浓密,就在狗前面加了一个毛,叫毛毛狗。直到 1949 年解放了,人家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我姥爷才不得不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先芝。
那一年,张先芝 12 岁。多巧呀,我们都在 12 岁那年,拥有了一个自己满意的名字。 雨素的母亲先芝
雨素的母亲先芝
我和她相似的地方很多,都很坚强。这个社会都是捧高踩低的,孩子失败了,父母也会跟着打击他。但我觉得我妈就这一点好,她永远不打击她的孩子,我小时候跑去海南岛三个月,一回到家,只有母亲还用慈祥的眼神爱着我。我离婚了带着两个孩子回家,母亲没有异样,只是沉着地说,不怕。在物质上,她给不了我一分钱,帮不了我一分忙,但她从不会说我一句不好,她会说,这算不了什么,你们慢慢做事,都能熬过去的。我给我两个女儿起的名字,也都是植物。没有特别的含义,就是生长,除此之外别无目的。不管她们做什么,我都很高兴。
现在,我一个女儿在工作,一个女儿在上大学,不在一个城市。五一的时候她们回来找我,我们一块去看电影。电影一点都不好看,但那个时刻,我觉得很幸福。
我认识的一个北京人说,每次看到这个品种的月季,就想到村姑。但我挺喜欢的,它有刺儿,很坚强,每次大雨大风以后,还是带着水珠很鲜艳地在那里,不会一刮就没。
我的微信头像是蜀葵,生命力特别强的花朵,农村每家房前屋后都种着。 雨素的微信头像我们老家镇上的诗人孟浩然,写过一句家喻户晓的诗:“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他听过的雨声我也听过,他看到的花落我也看过,他为花惋惜,我们是相通的。如果有可能,我也希望我们身上的生命力,也永远不被冲刷掉。
雨素的微信头像我们老家镇上的诗人孟浩然,写过一句家喻户晓的诗:“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他听过的雨声我也听过,他看到的花落我也看过,他为花惋惜,我们是相通的。如果有可能,我也希望我们身上的生命力,也永远不被冲刷掉。
我现在还在皮村住着,房租从 300 块涨到 600 块。我吃很多,看书比干体力活还费粮食,看书看完就饿,饿得难受。
最近接了两个约稿,一个是写关于流动儿童的非虚构,还有一个奇幻小说,我每天都在都在琢磨,比每天擦玻璃、擦家具、抱小孩还累。
干那活对我来说就是肌肉记忆,但写作就是精神压力,要是写出来跟小学生抄生字一样,拿不出手呀。你答应了的事又不能推,不按时交稿在别人眼里还不靠谱。
我也不是那种不果断的人,为什么不拒绝。后来我想了很久,想明白了,生命也需要破茧成蝶,生命需要创造,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我现在有两条白裙子,一条自己买的,一条是大女儿给的,她不想穿了就送给我。
但只要裙子还在,我的梦就还在。只要我的名字还在,梦与路就同在。小时候离我们家三里路有个火车站,后来,我就坐上了那列绿皮火车。而且皮村挨着首都机场,十多年前我耳朵里都是飞机的声音,嗡嗡响,后来已经习惯了。“我喜欢坐飞机”
现在我就梦想去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看看,我总觉得,我跟堂吉诃德有点像,只要我们做梦,生命就会留下点什么。《堂吉诃德》和《包法利夫人》,都是主人公看了骑士小说、言情小说,学着小说主人公的样子生活,《堂吉诃德》是喜剧,《包法利夫人》是悲剧。其实生命就是这样的,不是喜剧,就是悲剧,并不复杂。好命、孬命都是无所谓的,生命的意义在于日复一日的模仿中。有创造,有新意,有意义。如果没有梦,可能永远没有人看到我的存在。雨素这个好听的名字,可能一生都没有人叫。人活着,就该做点跟衣食住行无关的事情。我写作就是为了向世界大声说,我存在。我的名字叫雨素,雨是濛濛细雨的雨,素是白裙子的素。
↓↓↓
雨素的母亲先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