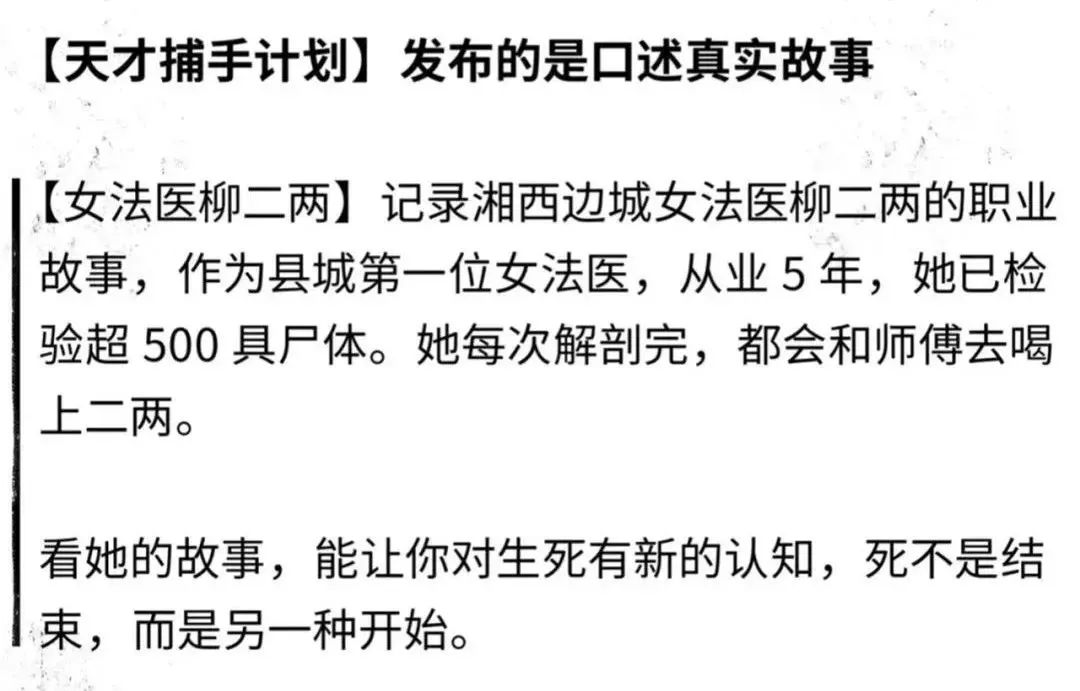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陈拙。
女法医柳二两告诉我,在他们那里,家里丢东西了,很多人就会去找“打时”,这实际上是算命寻物的一种。“打时”不止能找小东西,还能找一些大的,比如尸体。有一次柳二两出命案现场时就撞见了这种方法,特邪门。现场围了很多人,还告诉柳二两,是打时的算到死者在“东南方向、水边”,他们就找来了,比警察还快。柳二两说,也有可能是经验,案子发生在夏天,游泳图凉快的人最多,溺水死的也多,水流在东南方向有湾口,尸体大概率会停在这里。很多事情只看表面是诡异,往深了看一层,就会有不同的理解。表面上看,是一个女人去算女儿考公能不能上岸,算命先生告诉她,你死了,你女儿就会顺利了。于是她跳河溺死了。但当你读完这个故事,也许会看到很多比鬼神更复杂的东西,比如,一个女人的一生。

2021年10月,我跑去当了一次伴娘,穿着香槟色的伴娘裙,跑前跑后地帮新娘提包,把她的婚鞋藏在窗帘上面,以示作为“娘家人”,想多留她哪怕一分钟。我和新娘吴瑷认识于一年多以前,她的朋友很多都不认识我,闲聊婚问我在哪里上班,我说公安局,对方顺着夸一句“警花啊”,我就嗯嗯答应,不再说话。这么喜庆的场合不太适合解释,我的工作是法医,我和吴瑷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刑警队,我领着她去辨认她妈妈的尸体。也是因为那起案件、因为那场死亡,我俩成了彼此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那天下午“麻友”李慧给我打来电话时,我正要下班,心情很好,接起电话语气也很轻快:“怎么想起我啦,周末打麻将不?”
感觉李慧在电话那头白了我一眼:“哎呀,不是,你脑子里就是麻将!”她语气焦灼,说有个朋友的妈妈昨天晚上不见了,今天上午也没回来,派出所说没有被害迹象,暂时不找,问我能不能帮忙找一下。我满口答应,匆匆看了一眼李慧发来的照片,就被喊去出现场了。钓鱼的在水电站大坝河边发现了一具女尸。赶到现场的时候,浮尸还在打捞。早春的风还很凉,水也冰凉,打捞尸体的工人划着船熟练地将尸体抬上岸,一边跟我们说:“这个女的有味(有意思),她还把个鞋子绑起的。”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女人脚上穿的鞋用黑色棉线绕了很多圈绑住,看起来不像平时走路的装束。细看鞋底,橡胶底棱角分明,几乎没有磨损。我心里有了些猜测,再看了一下女人身上穿的衣服裤子,长袖T恤、薄羽绒服外套、运动裤,虽然不是什么牌子,但看起来都很新:“师父,这是不自杀啊,一身都好像是新衣服。”知道自己会死,想漂漂亮亮地走,所以穿了新衣服,还用棉线把鞋拴在脚上,防止顺水漂流过程中鞋子掉了。感觉这个女死者还挺讲究的。按规定,我们把基本信息交给同事去找人后,就把尸体带回了公安局,做进一步检查。给她脱外套时,在雪亮的灯光下,我意外地发现衣服内侧、胸口位置有一个缝死的夹层,像武侠小说里那种暗袋一样。我用柳叶刀划开针脚,从里面取出一个三角形的纸包,手掌大小,薄薄的,很轻,被胶带缠了几圈。胶带应该是防水用的,里面装着什么?遗书?
师傅给我递来了毛巾,我换下湿漉漉的手套,用干毛巾擦去表面残水,在手术垫单上操作。胶带的起始点一般会有使用胶带人的脱落细胞或者指纹,可能会是案件突破口,我小心地找到源头,提取了脱落细胞后,用柳叶刀划开胶带。内层是个塑料袋,我继续划开,最里面是个叠成三角形的黄色纸条。一打开,妈妈呀,是个符!上面画着我看不懂的红色线条。我脑子里一下闪过看过的各种恐怖片、诅咒什么的,认真反思了一下从接触死者至今有没有做什么不敬的举动,好像没有吧?跟符叠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小纸条,纸上写着:“穿寿衣后,用黑线挂我脖子上。”应该是指这个符。如果这个女人是自杀的,那这就是她全部的遗言,没有一句跟她的身份、家人有关,也没有一句提到自杀的原因。她似乎以为没有人会找她、会认出她,唯一的遗愿,好像是写给打捞起她的陌生人:希望死后能给她穿寿衣、挂着符。
我和师父正对着符百思不得其解,就听到解剖室外喧闹起来,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跟一个大伯相互搀扶着,直接要往解剖室里进,口中喊着:“在哪里?”在门口的同事问了一句“你们是家属?”,女孩带着哭腔点头嗯了一声,继续走近。待看清死者的脸,她立马绷不住了,扭头埋在男子的肩膀上哇哇大哭,口中念着:“是妈妈,真的是妈妈……”带他们来的派出所同事告诉我,这俩人是父女,昨天就报过案,说是家里的女主人、50岁的徐丽芬彻夜未归。年龄、时间都相符,所以让他们来认一下人。等等,这么巧的吗?我赶忙掏出手机看下午李慧给我发的寻人启事,之前匆匆一眼根本没记住照片什么样,这么一看,除了发色不同,不就是一个人嘛。照片上女人的头发是发根是黑白相间的,发尾有一点点黄色,死者的头发则是全染黄的。很有可能是自杀前专程补染的,和她买新衣服的动作也相应。李慧还给我发了条消息我没看见:“派出所说在河边找到了,是不是正好是你刚出去?”我心里有点点愧疚,要是我不这么脸盲,是不是就可以早点回个消息,别让人家亲生女儿来认脸,这伤害多大啊。这么想着,我主动上前跟女孩搭话:“你,你好,我是法医,你是吴瑷吧,刚刚李慧找我帮你找妈妈,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之前师父都会跟家属说“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结果”,我也说了,吴瑷还是哭着。我没招了,想转移她的注意力,把符和纸条拿了出来:“这是我们刚从你妈妈衣服上找到的,你认得吗?”吴瑷眼神充满疑惑地摇了摇头,她爸爸也带着点埋怨地说:“你妈妈这是搞的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晓得。”吴爸爸说不记得了,吴瑷却立马说:“是新衣服,她平时穿的就那么几件。”还是女儿心细。我又说:“鞋子很明显是新的,还有绳子这样绑着的,应该是怕水冲走。”我委婉地暗示这可能意味着自杀:“你妈妈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吴爸爸反应过来,但神情更迷茫了:“她是怎么想不开了……”他说最近家里没遇到任何事啊,妻子平时就去超市上上班,看不出什么不对劲。自杀总该有个缘由吧,我有点奇怪,再次进行检查,还是没有找到任何他杀的迹象。按程序,我能做的做完了,只能通知吴瑷父女俩先把尸体接走。看到吴瑷眼睛红红的,我尽量用了个委婉的说法:“一块石头抛上天,最终要落地,事情发生了,没办法,最终还是要面对。你们可以先给阿姨把衣服(寿衣)穿上。”听到这句话,本来情绪稳定一点的吴瑷突然又哭了起来,吴爸爸帮着答应:“要得。”我和吴瑷加了微信。以前加家属微信这种事情我最抵触了,但今天看到她哭,我总感觉心里也有点难过。吴瑷给我发来好友申请,头像是只可爱的小狗,微信名是个太阳。点开朋友圈,最近一条是今早发的寻人启事。寻人启事上配的照片是彩色的。那是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田,一个阿姨站在花田中间,穿着出去玩才穿的鲜艳衣服,仰起脸,灿烂地笑着。也许是因为笑容,整张脸年轻了十岁不止。下午,痕检员找找问我“去不去你的小姐妹家看看”,他说队上担心那个符跟什么邪教有关,要去搜一下。我立马跟去了。吴瑷家是一座两层的县城私房,吴瑷把我们领到二楼,徐丽芬的房间。这种房子光线总是很昏暗,她打开灯。整个房间还是有人住的样子,没来得及收拾。床上铺着老式上海牡丹花床单,不配套的花被子折得整整齐齐。没有疑似宗教的神像之类的,而且一切都收拾得干净整洁又有生活气息,毫无异常。痕检员找找打开床头柜的抽屉,发现最上面有一张纸条,吴瑷跟着我们,看到纸条立马一把抢过去。我凑在她后面看,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着:“妈妈的生命不值什么,一切都是希望你好”。
这纸条似乎和跟符一起的纸条是同一个来源。还真是遗书?吴瑷翻来覆去,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话语,没有了,她笑起来:“又是为我好。”可是她只是发出了笑的声音,眼泪又从红红的眼睛流下来。我又蹲到床头柜翻了一下,原本放着纸条的地方,下面是一本厚厚的家庭相册,大部分都是吴瑷小时候的照片,还是胶卷的,在那个年代得值不少钱吧。我感觉这里面有事。偷看一眼找找,他那个直男,面对女孩哭泣,直接躲避眼神,继续找东西去了。只剩我了,我想了想是不是该抱抱吴瑷,又考虑到自己戴着手套,虽然是干净的但总是有点不好,于是翘起两只手向吴瑷拥过去。我感觉到吴瑷本来哭泣颤抖的身体一僵,我也很尴尬,立马退开了。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吴爸爸拯救了我们,他从楼下上来,叫吴瑷过去,“你姨来了,说有事要跟你说”。找找没有找到什么邪教相关的资料,我们一起下楼了。堂屋里,一个跟吴瑷妈妈长得很像的女人正哭着,吴瑷叫了她一声,她抱着吴瑷又哭了一会,突然说:“瑷丫头,听说你妈走的时候身上还有个符,是姨对不起你。”吴瑷好像想打断她,带着哭腔说,是我妈自己选择的,跟其他人没关系。我很想把姨的话听完,跟着吴瑷也叫了声姨:“姨,我们是公安局的,也是吴瑷的伙计,你是不是知道这个符和吴瑷妈妈的离开有关系?”女人看了吴瑷一眼,吴瑷点点头,她才断断续续地说,她可能知道这个符是哪来的。吴瑷的姨告诉我们,年前有一次,徐丽芬约她去找算命先生,因为吴瑷在家准备公务员考试,徐丽芬想给女儿问问前程。那个算命先生很神,她们只给了吴瑷的八字,人家就算出来这个人没有兄弟姐妹,本来应该是个拿枪的,可惜小时候没有照顾好。吴瑷还真的是个独生女,也真的参加过高考军警体检,是因为感冒诱发哮喘没有过。都给他算中了。但是后面这个算命先生又说,这个孩子跟她妈妈八字相克,如果没有妈妈,今后事业和婚姻都会比较顺利,否则还要经历一番波折。吴瑷姨当时就反驳了:“你这个算命的,她娘在这里,哪里有你这么说话的?!”算命的被她训得不抬头。她拉着徐丽芬要走,徐丽芬却不走,很平静地对算命先生说:“那要我怎么办呢?有解吗?”徐丽芬竟然就这么信了,听到这里我就一呆。有哪里不对劲,这不像是被算命的吓的,更像是心里早有这个想法,被算命的说中了。吴瑷姨说,后来徐丽芬就花钱跟算命先生买了那个符,算命先生说符要随身携带,“带到棺材里,可能保你丫头的婚姻和事业一头。保两头,你和你丫头相克,我这里办不到。”吴瑷姨当时没觉得徐丽芬真的把这当回事了,以为就是花钱买个心安。徐丽芬叮嘱她别告诉马上考试的吴瑷,她就没说,没想到出了这事。吴瑷姨抱着吴瑷痛哭:“你不要怪你妈妈,你妈这辈子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吴瑷的语气近乎崩溃:“神经病,我妈真的有神经病!”我也觉得好不可思议。一般算出这种不吉利的东西,我们就会再找个道士“破”一下,不会傻傻地听他的,就算真的信了这个道士,省考还没定是哪天呢,为什么昨天就自杀了?
第二天一早,我收到通知去参加徐丽芬案的结案汇报。吴瑷和她父亲、舅舅、大姨坐在了我们对面。同事播放了找到的监控证据,也就是徐丽芬生前的最后一段路。监控摄像头拍到,她准点走出了超市的大门,接着就一个人在街上绕,没有跟人说话,也没有去买什么东西,最后走到了桥上。她在桥上呆了很久,一直到夜色降临,人变成了一个黑影,黑影从桥上一跃而下。超市员工都表示,没有人和徐丽芬产生冲突,加上徐丽芬的新衣服是早上出门就穿好的,也排除了工作矛盾导致自杀的怀疑。如果算上徐丽芬染发的时间,这个决心大概下得更早。徐丽芬在没有遇到任何意外、没有被任何人威逼的情况下,选择了死亡。领导向吴瑷家人给出了自杀的最终结论。这段视频虽然可以解释所有法律上的东西,但对于家人来说,大概是更大的谜团。吴瑷的哭声好像在问:“为什么?”家人们彼此搀扶着走出公安局。如果没有意外,这大概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我忍不住追上去对吴瑷说:“你好好的,你和爸爸是彼此的依靠了。”她点点头没有说什么。看来和前几次一样,我的安慰还是没有起效。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中午的时候,“麻友”李慧又打来电话,问我可不可以陪她去看看吴瑷,“明天她妈妈就送上山了,今天晚上她肯定要守通宵,我想陪陪她,晚上我又有点怕”。我二话不说答应。去的路上,李慧告诉我,吴瑷跟她是高中同学,俩人每天放学一起回家。“其实吴瑷是个蛮好的人,说不出具体的事,没有那么多脾气和弯弯绕绕的花花肠子。”但是后来高考的时候,她们几个关系好的都读了湖南本省大学,就吴瑷一定要去外地上学,联系就少了。我问李慧知不知道吴瑷为什么要考出去?李慧含糊地说,好像是不想再被家里管了吧。吴瑷不喜欢呆在家里?我赶紧追问:“你觉得她跟她妈妈关系怎么样?”李慧说小时候她们没聊过这些,去年吴瑷回来考公务员以后,跟她抱怨过几回。吴瑷回来得匆忙,年前国考成绩不行,她妈妈好像就经常说她,只要她没在看书,就骂“我怎么生了个寄生虫”,或者说她是借口躲在家里不工作什么的。我暗自吃惊。徐丽芬不是很爱女儿的吗,小时候的照片都留着,还写了那样的遗书。为什么在吴瑷口中却是这样的?李慧也跟我打听吴瑷母亲自杀的事,我欲言又止,说你到时候听吴瑷说吧,也让她把心里话说出来。

晚上七点多,我和李慧到了吴瑷家,吴瑷头戴着长长的孝帕,腰间系着根稻草绳,正跟着道士作揖。我终于不再穿着制服,而是以一位朋友的身份来了,这次,我的眼眶没有负担地红了。吴瑷冲我们点头示意,李慧上去拥抱她:“小瑷同学,我来陪陪你。”吴瑷垂着手没有回应,让我们先坐。我和李慧在一楼找了个地方坐下,非亲属的除了我们只有几个邻居。吴瑷的姨和舅舅不能像后代一样参与法事,正静静坐在堂屋的棺材旁边。舅舅时不时点根烟。法事很冗长,道士挥着我不认识的道具,唱着我听不懂的经文,屋外的招魂幡也一摇一摇的,我都感觉有点害怕,又想到如果我们没来,吴瑷一个人会不会怕?吴瑷是独生,法事的大部分环节都是要由亡人子女参与的,她就一个人站在堂屋中间,垂着眼睛,表情好平静。过了12点,法事终于告一段落,吴瑷走过来跟我们说了第一句话:“谢谢你们两个来陪我。”她劝我们回去休息,说这也没什么事需要帮忙。但我就觉得自己得在,坚持说,我们靠椅子上眯一会就好了,赶她去休息。我和李慧坐了一会,半梦半醒时,听见堂屋传来细细的说话声。吴瑷、吴爸爸和姨姨还有舅舅都坐在棺材旁边了,火光映在他们脸上,他们在说徐丽芬。开始是吴瑷父亲带着玩笑的语气说着和徐丽芬当年相亲认识的事:“刚认识的时候看起来好温柔,哪知道结婚了把我欺负得好厉害,烟也不让抽。”他对吴瑷说,可能你不知道,年轻的时候我有次在工地结不到工钱,是你妈自己跑去找老板大吵大闹,老板没得办法才结了账。吴瑷父亲学着徐丽芬的语气:“‘你们家养孩子我们家也养孩子,不给钱的话,我就天天来找你!’”他们口中的徐丽芬,似乎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她会拿着棍子找逃学的弟弟,找到了就是一顿抽。会管家里的钱,着急了能跟老公干。只有吴瑷姨一直在说“不是不是”,她说徐丽芬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小时候徐丽芬很好笑的,总管她叫姐姐,明明自己才是老大。吴瑷问为什么?吴瑷姨说,可能是因为“姐姐”要干活吧。那时候俩人一起放学,小徐丽芬总会提议俩人轮着背书包,“快到家了,她把我们两个的包都背到,爸爸还以为她帮我们背了一路”。吴瑷姨叹息着说,“我其实读书不如你妈,但是我那时候太小了”,“那时候”,也就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吴瑷舅舅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忙,一定得有人辍学照顾弟弟,最后就是徐丽芬。吴瑷姨还记得,最开始徐丽芬“一直不服气”,等把弟弟带大了,她没再提过那些话。她好像已经适应了大姐这个身份,揍弟弟,也会把挣的钱都给弟弟买零食;收拾丈夫,但这么多年没嫌过丈夫穷、闷,没让丈夫沾手过家务。徐丽芬永远有办法、永远靠得住,直到“突然”自杀前,都是这样。

我很想听他们会不会聊一聊徐丽芬自杀的原因,哪怕是关于徐丽芬和吴瑷的母女关系,但他们一句也没有提,就连吴瑷也没有提。实际上,她根本没有主动聊起妈妈,只是一直在和家人们追问那些她没出生时的事情。我突然想起,在我们的风俗里,人死了不是真的“走了”,她的魂魄会徘徊在家里,直到落葬。所以下葬前的这晚,才是人在世间最后的时间。一直聊到道士们都睡醒了,又开始呜哩哇啦地唱,盖过了说话的声音,大家就都去睡了。我也靠在椅子上睡了几次,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被人叫醒。晨雾里,送葬的队伍缓缓往山上走着。吴瑷穿着孝袍跟在棺材后面,我和李慧远远地跟着,雾气和纸钱烧下的灰不断扑到我们脸上。封棺落土,是我们风俗里这个人真正“走了”的时刻。那一刻,我看到了这个同龄女孩真正最崩溃的样子,整个人哭得趴到了泥地里,手指往坟墓的地方一直抠。我感觉自己也在流眼泪。解剖过那么多具尸体,可我也从来不明白死亡是什么,只能站在这里,当作自己陪过她了。一切结束到下山,已经是八九点钟。我和李慧打算自己回去了,吴瑷从人群中跑出来,拦住我们,专门说了一声谢谢。她好像有很多话想说,但眼睛红红的,整个人疲惫得快散架了,最后只是约我们晚上一起吃顿饭。我回家补了一觉,醒来就看吴瑷给我发了个烧烤摊的地址。我和李慧过去的时候,她已经点好串串等我们了。吴瑷眼睛还是肿肿的,见我们到来,有气无力努力地笑着:“我也不知道你们要吃什么,李慧喜欢吃肉,反正各种肉串还有牛油都点了,你们看看还要什么。”我和李慧都被吓了一跳,对视了一眼。吴瑷还是没事人一样,问我们喝什么,又微笑着跟老板道谢。李慧拿起小酒瓶拧开往吴瑷杯子里倒酒:“小瑷同学,我们从高中就认识,那时候一起放学回家,没想到时间一下就过去了,今天难得约在一起喝酒,我们不醉不归。”我小心看着吴瑷的表情,吴瑷噙着眼泪微笑:“是的,一晃好多年了。”说着一仰头,一杯一两的杯子一下去了一大半。我赶紧碰了下她的杯子:“慢点喝,慢点喝,咱们细水长流。”吴瑷摆了摆手,她说我知道你说喝酒是什么意思,就是希望我能缓解下情绪,“我没事,我这几天一直在想算命的说的话,可能我和我妈真的相克,我认命。”李慧还不知道算命的事,吴瑷大概讲了一遍,她一听就毛了:“那是哪个算命的说的,把他家掀了去!”吴瑷摇摇手说哪里找去。我们又喝了一会,吴瑷渐渐的有点醉了,脸红红地说:“说句没良心的话,我感觉我妈去世了,我很轻松。”吴瑷举着杯子,把头埋在胳膊里摇头:“不是的,我没醉,我这话没办法跟家里人说,我是真的感受到解脱。”

她说就她回来的这一年多,感觉日子好痛苦好痛苦,每天妈妈都在埋怨她,埋怨她为什么上次没考上,为什么早不考。过年期间,她不想起大早去走亲戚,妈妈就骂她在家啃老,“不去也好,带出去也丢人!”。她反驳说自己吃喝一直用的存款,要不让住她就走,她妈又不让她收拾东西,俩人扯得差点打架,还是被她爸劝开的。后来她妈来找她道歉,用的话是:“我对你不好吗?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为什么过年一起出去玩都不能听我的?”“我真是听得好笑。我跟她说你要什么都听你的,养条狗吧。”“总是这样、总是这样”,小时候明明说好考了双百就买公主裙,考到了却又指责她不知道心疼父母,“你有衣服穿,妈妈到超市打工,爸爸当电工,赚钱不容易,要你考双百是为你以后能有出息,不像我们一样。”上大学她谈了男朋友,这个嫌矮,那个嫌穷,她问妈妈为什么永远不满意,妈妈最后说,“我就是不想你嫁太远,以后见不着”。她在外面工作时遇到了性骚扰,上司故意摸她的手,要求一起出差,她是逃回家考公务员的,可是妈妈反过来责怪她说,早让你考你不考,“现在在外面荡一圈了回来又考,是不是耽误时间?”昨天夜里,我在火炉边听到的那个要强的、照顾所有人的徐丽芬,在女儿面前,竟然是这样的。守灵夜的谈话,他们只说了温馨的一面,其实那些“拿棍子逼着弟弟上学”、“不准丈夫抽烟”,不也算是一种“刀子嘴豆腐心”的打压方式吗?只是这一切在吴瑷身上变本加厉了,成为沉重的负担。吴瑷说,其实几乎每次吵架,妈妈都会低头,来敲门问她“我做错什么了”。她会不忍心,告诉妈妈自己因为什么生气。妈妈会承诺以后会改,尽量不这样说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下一次又照旧。过年期间吵那一架也是这样,徐丽芬骂完她没出息,又来问她:“你为什么跟妈妈不亲?”语气很委屈。那之后,直到自杀前,她们没有争执,也没有再说什么话。我心里好像闪过一道惊雷。我突然明白徐丽芬是怎么想的。她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一说话女儿就难受,她无法理解女儿讨厌的究竟是一种说话方式还是她本身,她只能理解为,算命的说得对,这是八字不合,她和女儿不能共存,她挡了女儿的路。就像初中那年辍学让弟弟上学;就像在家照顾孩子让丈夫上班。牺牲是她最习惯的一件事,她是长姐、妻子、母亲,她习惯了,“我的命不值得什么”。
她值得的,她那么勇敢、厉害,她那么爱她的所有家人,她问过那么多次“我做错了什么”……她真的很想改的,她很想爱她的女儿的。困住她的不是那个符,而是五十年来,家庭给这个女人划出的一条道路。

不知道是感同身受还是酒精发作,我也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李慧看我俩都哭了,大喊大叫着哄我们:“哪有这样的事啊,当父母的总想着控制孩子,美其名曰听话孝顺,狗屁!”饭店老板在那边听不下去了:“你们这几个丫头搞什么,哭啊笑的,当父母的肯定要把孩子管着啊,孩子走了,没人养老,不然白养了,你们明儿了当父母了就知道了的。”我白了一眼老板:“你这种当父母的心思要不得,我也不可能当这种父母。”烧烤店老板的儿子也在旁边有样学样地叫:“是的是的,你只要我听你的,我长得有脑壳。”我蹲下来摸着小孩的头:“弟弟,你爸要欺负你,要勇敢反抗,我支持你!”老板扯过他的儿子:“几点了,还不回去睡觉!我等下扇你两下!”一脚把他儿子朝家的方向踢走了。笑完了,吴瑷呆呆地叹了一口气:“我真的好喜欢妈妈心情好、听我分享校园趣事的时候,她会追问我真的吗?然后我就又给她说一遍,又说一遍。”我猛地喝了一大口酒。我们都不再说话,一杯又一杯,河水静静地流向夜。后来,我们三人有了一个微信群。吴瑷决定留在家里继续考公,我们经常一起吐槽,一起帮吴瑷备考。我割扁桃体,她在我病床旁吃臭豆腐,我们一起吃吃喝喝,买漂亮衣服。通过笔试、通过资格审查,到最后上岸,每个新消息她都兴高采烈地汇报给我们,我们乐呵呵地鼓励她。第二年,吴瑷要结婚了。我跑到她家当伴娘,忙前忙后,一直闹到晚上,还留下来收拾。堂屋乱糟糟的,都是彩带和纸花,我突然注意到正中间挂了一幅十字绣,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新添的,针脚好漂亮。我呆呆地看了很久,吴瑷爸爸看我发呆,笑着说了一句,这是吴瑷妈妈绣的。
这个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徐丽芬问的那几个问题:“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为什么和我不亲?”而她的女儿也曾经一遍一遍地向她回答:“你能不能不要那样说我?”“你能不能像别的妈妈一样当我的朋友?”这段对话让我很难过。她们都曾经非常努力,可却好像站在河两岸,听不见彼此说话。在徐丽芬生命的前五十年,她曾用自己的牺牲和强势,鞭策家人、保护家人,但到了女儿长大那一天她才发现,这一套不再通用了。她是那个年代扛起整个家的女性,面对贫穷、饥饿、拖欠工资、居无定所,她永远有办法,而这一刻,她没有办法了,她改不了自己。她决定去死。我们无法苛责吴瑷或者任何和她一样的子女,在自己感到被打压、感到痛苦时,仍然不计回报地去爱父母;但我也希望,这个故事能让更多人看见,那些在“施暴”的人,被困在什么样的局限里。
插图:大五花
本篇9990字
你已沉浸阅读约19分钟
如果你想阅读【女法医柳二两】的更多故事,可以点击下方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