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自:实验影像工作室
 《沉默的真相》,摄影,尺寸可变,2017年
《沉默的真相》,摄影,尺寸可变,2017年
撰文:海杰
本文为《中国当代摄影图录:董钧》(浙江摄影出版社)评论文章
“图像……是时间的遗产”,当董钧说出这句话时,意味着他的图像要么往返于历史的迷雾之间,要么是在抽象的时间堆叠之河里泅游。前者,我们可以看到《贫乏于世的它性》(2018-2020)、《长安诗译考》(2022),而后者,几乎是他作品的普遍基底。
我们不妨回到他的创作之初。《沉默的真相》(2003至今)系列里,类纪实摄影的黑白环境肖像,既是对人的考察与凝视,也是对人的病理的释放与展示。不管是两个戴着游客的遮阳帽,表情成人化的小孩,或者是一个坐在地上抽烟,而另一个斜躺,靠左肘支撑身体也在抽烟男人,抑或在少数民族地区被敬酒的场面,我们都可以看出一种日常状态的出离,而进入到特定的被审视的空间中去。人进入了某种剧场,他们的面目具有了表演性,这个剧场不是我们认为的表演空间,而是人在脱离生活空间后的一种放飞状态。所以,艺术家的镜头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进行了及时准确地捕捉。在其中,贫穷被裸露,油腻的中年被戏剧化展示,而游客凝视的场域被他升格为马戏团般的怪诞场景,幽默又如影随影地潜入到各种景点的雕像中去。这组作品时间跨度有20年之久,所以可以想见,这个被命名为《沉默的真相》的作品里,时间如何残酷地穿过,并携带着艺术家不同时期的感受与认知。 《沉默的真相》,摄影,尺寸可变,2003年
《沉默的真相》,摄影,尺寸可变,2003年
 《沉默的真相》,摄影,尺寸可变,2003年
《沉默的真相》,摄影,尺寸可变,2003年
 《沉默的真相》,摄影,尺寸可变,2021年
《沉默的真相》,摄影,尺寸可变,2021年

《沉默的真相》,摄影,尺寸可变,2020年

《沉默的真相》,摄影,尺寸可变,2019年他终归感兴趣的还是人。比如《对视》系列之“模特儿”(2005),这些面孔承载了病痛与贫穷的“模特儿”,面对的不再是被一群人从不同角度进行环视的艺术道具,而是选择直视镜头,让观众也在面对这些肖像时也没法躲闪,被这种表情中的忧伤、苦难抑或是疑问所吞没,或者劫掠。这组肖像的语言是暴烈而短兵相接的,我很好奇艺术家为什么反而采用方画幅这种缓慢的图像采集方式。当他们不再作为被凝视的对象,而回到自身的命运时,展示出的面孔的表述是强劲而疼痛的,以至于我们很难长时间与其对视。
而另一个《对视》系列之“NEXT CHINA”(2006),他选择的是少年,“NEXT CHINA”是预警,还是期待?他把每一个少年都放置在圆形的画幅里,这种中国传统文人水墨的创作尺幅,某种程度上是豢养的以供消费和把玩的尺幅,这种语言的使用对于董钧来说,意味着什么,与他们的对视是否是一种平等的对视?他们作为一种集体的话语表述,通常是成人们玩弄话语的承载对象,如今在艺术家的这种呈现中,是否本身就携带着这种思考? 《模特》,摄影,180cmx180cm,2005年
《模特》,摄影,180cmx180cm,2005年
 《模特》,摄影,180cmx180cm,2005年
《模特》,摄影,180cmx180cm,2005年
 《模特》,摄影,180cmx180cm,2005年
《模特》,摄影,180cmx180cm,2005年
《Next China》,摄影,120cmx120cm,2006年
《Next China》,摄影,120cmx120cm,2006年
《Next China》,摄影,120cmx120cm,2006年
藉由“真相”展开的创作,是缠绕董钧的思虑,也是他作品屡试不爽的讨论的核心,从《沉默的真相》开始,到纪录片《大水》(2007-2008),再到后来他沉寂多年,推出的多媒介作品《两生花》,真相的思考由单纯的摄影变为多角度多媒介的开放式创作。《大水》,纪录电影,海报,180Min,2008年 《大水》,纪录电影,剧照,180Min,2008年
《大水》,纪录电影,剧照,180Min,2008年
《大水》,纪录电影,剧照,180Min,2008年即便是在《贫乏于世的它性》,这样一个意外的转向“动物”的作品,也在图像和哲学的层面展开“消亡”的话题讨论,他再一次触及了“时间遗产”这一议题:“‘动物’更像是一个与人类共生弥久的时间遗产,我试图通过镜头和它们相遇在现实与历史中,也相识在真实与虚幻里。”动物在现实世界里,变成了人类的赘述,成为符号,他们不会死亡,甚至会永生,活在盆景、木刻、玩具、绘画、标本、餐盘、景点等人类所有能够欢愉的空间和媒介上,甚至,它们以死来表述生。人类对动物的描述和转译是孜孜不倦的,他们屏蔽了动物的动物性,而让其成为人类的一个凝视的符号。与其说是贫乏于世,不如说是“丰富于视”。而“它性”被改造成为“符号性”。
 《贫乏于世的它性》,幻灯摄影,尺寸可变,2016年
《贫乏于世的它性》,幻灯摄影,尺寸可变,2016年 《贫乏于世的它性》,幻灯摄影,尺寸可变,2020年
《贫乏于世的它性》,幻灯摄影,尺寸可变,2020年 《贫乏于世的它性》,幻灯摄影,尺寸可变,2020年
《贫乏于世的它性》,幻灯摄影,尺寸可变,2020年 《贫乏于世的它性》,幻灯摄影,尺寸可变,2021年在《两生花》这个作品里,董钧几乎摊开了他对于“真相”在创作中遮遮掩掩的疑虑。由一个文本《熟人识得蓬山客,却道心底两生花》展开,而由众多女性根据文本摘取演绎的图像构成的《两生花》,基于女性生活的亮面和内心的暗面互相交叉叙述进行的矛盾体,让观众体会了模糊的身份与语言。而附着于其上的其他作品涉及了摄影、影像装置以及文字,文字是其作品指向的哲学注解,“谁也看不见我泳镜里的泪水”既是主体影像的旁白,又是另外的影像装置《谁也看不见我泳镜里的泪水》的题目,同样也是文字装置“谁也看不见我泳镜里的泪水”的主体本身,“看不见”作为世界的常态,也是“真相”的屏障,而泪水就一定真相吗?泳池里肢体舒展的欢愉与深藏于泳镜之下的创痛始终纠缠于董钧这个复杂的作品之中。文字主导着这个作品,基于文本,又在作品各处闪烁,文字作为影像之舌,言说着基于影像的哲学的深奥议题,对于观众来说,观看和理解这个作品,本身也是在体验世界的迷幻与纠结。而在摄影部分的作品中,水的波纹被照射在洞穴岩壁之上的纹理,几乎是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的图像注解,这个很早就开启了“真实”之问的洞穴理论,是董钧一直以来对于“真相”的白热化处理。很显然,这不是作品表象上单纯的女性化叙事,而是以这样一个幽怨而有些嗔怪的女性化叙事,展示他对于几乎要在自己心里长出藤蔓的“真实”的具象化的显现。
《贫乏于世的它性》,幻灯摄影,尺寸可变,2021年在《两生花》这个作品里,董钧几乎摊开了他对于“真相”在创作中遮遮掩掩的疑虑。由一个文本《熟人识得蓬山客,却道心底两生花》展开,而由众多女性根据文本摘取演绎的图像构成的《两生花》,基于女性生活的亮面和内心的暗面互相交叉叙述进行的矛盾体,让观众体会了模糊的身份与语言。而附着于其上的其他作品涉及了摄影、影像装置以及文字,文字是其作品指向的哲学注解,“谁也看不见我泳镜里的泪水”既是主体影像的旁白,又是另外的影像装置《谁也看不见我泳镜里的泪水》的题目,同样也是文字装置“谁也看不见我泳镜里的泪水”的主体本身,“看不见”作为世界的常态,也是“真相”的屏障,而泪水就一定真相吗?泳池里肢体舒展的欢愉与深藏于泳镜之下的创痛始终纠缠于董钧这个复杂的作品之中。文字主导着这个作品,基于文本,又在作品各处闪烁,文字作为影像之舌,言说着基于影像的哲学的深奥议题,对于观众来说,观看和理解这个作品,本身也是在体验世界的迷幻与纠结。而在摄影部分的作品中,水的波纹被照射在洞穴岩壁之上的纹理,几乎是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的图像注解,这个很早就开启了“真实”之问的洞穴理论,是董钧一直以来对于“真相”的白热化处理。很显然,这不是作品表象上单纯的女性化叙事,而是以这样一个幽怨而有些嗔怪的女性化叙事,展示他对于几乎要在自己心里长出藤蔓的“真实”的具象化的显现。在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董钧所有作品中最复杂,且最敏锐,更是弥漫着情感和体验的作品。

《两生花》个展,展览现场,西安美术馆,2020年
 《谁也看不见我泳镜里的泪水》,三屏道影像装置,展览现场,2020年
《谁也看不见我泳镜里的泪水》,三屏道影像装置,展览现场,2020年 《无人知晓》,三屏道影像装置,展览现场,2020年
《无人知晓》,三屏道影像装置,展览现场,2020年
《两个故事》,摄影,110cmx170cm,展览现场,2020年
 《熟人识得蓬山客,却道心底两生花》,双通道录像,18Min,2021年如果说,这样的作品还让我们在这个由艺术家设置的迷局里心心念念没有走出的话,董钧已经在《长安诗译考》里跳入到唐诗在历史叙述中的现实考古。这个作品的宏大与历史的地域依赖,让我们这些从他的脉络一路走来的观众有些错愕,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转变与落脚?而大画幅针孔摄影这个摄影语言的选择,却又是一个由小入大的微观视角。艺术家通过对全唐诗的反复解读梳理出三个学术观点,同样是三种处世方式,对应的是送别、隐世和入世的古典生活方式。但历史的典故如何投射到现实之中呢?艺术家使用针孔相机大画幅底片是想借用历史景观的这个“针孔”重现历史的大画幅画卷,但历史一路走来,在时间的堆叠中,现实或许早已变得物非人也非。我们看到的“灞桥别离”的主体场景灞桥依然是工业化的水泥桥,长时间曝光里,河面平静,河边的树影影绰绰,小径短促,历史的遗址更是如同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结合部的一角。而“曲江应制”的场景显得体面多了,毕竟是皇家园林,一条长廊眼神到远处的楼阁,干净而低沉,只是这样的景致经历时间的淘洗,大致是现代人所寻古再造。而在“终南遁隐”里,被树群遮挡的终南山隐隐约约,遥远而又虚幻。如此大费周章的根据诗歌进行的图像考古,是艺术家以历史作为窥镜的当代观测,也是对于今人如何看待历史以及历史中文人、隐士以及皇室的时代境遇的测试。
《熟人识得蓬山客,却道心底两生花》,双通道录像,18Min,2021年如果说,这样的作品还让我们在这个由艺术家设置的迷局里心心念念没有走出的话,董钧已经在《长安诗译考》里跳入到唐诗在历史叙述中的现实考古。这个作品的宏大与历史的地域依赖,让我们这些从他的脉络一路走来的观众有些错愕,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转变与落脚?而大画幅针孔摄影这个摄影语言的选择,却又是一个由小入大的微观视角。艺术家通过对全唐诗的反复解读梳理出三个学术观点,同样是三种处世方式,对应的是送别、隐世和入世的古典生活方式。但历史的典故如何投射到现实之中呢?艺术家使用针孔相机大画幅底片是想借用历史景观的这个“针孔”重现历史的大画幅画卷,但历史一路走来,在时间的堆叠中,现实或许早已变得物非人也非。我们看到的“灞桥别离”的主体场景灞桥依然是工业化的水泥桥,长时间曝光里,河面平静,河边的树影影绰绰,小径短促,历史的遗址更是如同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结合部的一角。而“曲江应制”的场景显得体面多了,毕竟是皇家园林,一条长廊眼神到远处的楼阁,干净而低沉,只是这样的景致经历时间的淘洗,大致是现代人所寻古再造。而在“终南遁隐”里,被树群遮挡的终南山隐隐约约,遥远而又虚幻。如此大费周章的根据诗歌进行的图像考古,是艺术家以历史作为窥镜的当代观测,也是对于今人如何看待历史以及历史中文人、隐士以及皇室的时代境遇的测试。

《长安诗译考》灞桥别离,超大画幅针孔摄影,独版印相,80cmx40cm,2022年

《长安诗译考》终南遁隐,超大画幅针孔摄影,独版印相,120cmx40cm,2022年

《长安诗译考》曲江应制,超大画幅针孔摄影,独版印相,135cmx40cm,2022年
历史本身是时间的遗产,大部分淘洗不复再现,而小一部分已然堆叠在诗歌里,进行转译,现实在时间的堆叠里,面容早已改变,但许多问题依然如迷雾一般穿越历史,复现当下。2023年8月20日写于燕郊

海杰,从事独立策展和影像批评,青岛电影学院摄影艺术与技术系学科带头人,燕京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受邀担任国内外多个艺术展与摄影节的评委、学术委员与提名人。出版多本学术著作,亦是1839摄影奖联合发起人兼学术总监。
董钧,艺术家、策展人、导演。1839摄影奖发起人。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影视动画系摄影专业主任。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亦为曾经中国重要的独立影展西安亚洲民间影像年度展、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的艺术总监与总策展人。《中国当代摄影图录》:由艺术家刘铮主编,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过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开放的中国造就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发展环境。就摄影艺术而言,中国有着众多优秀的创作者涌现,他们与全球各地的摄影艺术家一起努力地探索和实践,成为世界摄影艺术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出于各种原因,中国摄影家的作品及其价值远远没能为全球所认识和关注。中国当代摄影的学术体系和发展脉络还未得到系统的梳理,摄影者的创作也经常被各类观点模糊的奖项所影响。《中国当代摄影图录》意在呈现众多的个体摄影创作案例,描绘出一幅中国当代摄影创作的全景画卷。这是一个必须去做的基础学术项目,也是一次充满挑战和未知的艰辛尝试。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套图录的意义将逐步显现出来,而且必将对今后中国摄影的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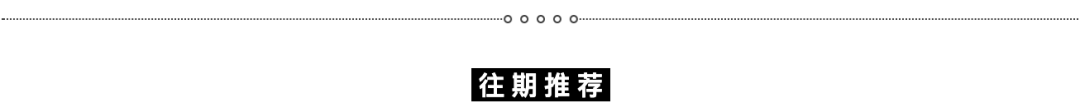
推广|合作|转载 加微信☞zhanglaodong
《沉默的真相》,摄影,尺寸可变,2017年
《沉默的真相》,摄影,尺寸可变,2003年
《沉默的真相》,摄影,尺寸可变,2003年
《沉默的真相》,摄影,尺寸可变,2021年
《模特》,摄影,180cmx180cm,2005年
《模特》,摄影,180cmx180cm,2005年
《大水》,纪录电影,剧照,180Min,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