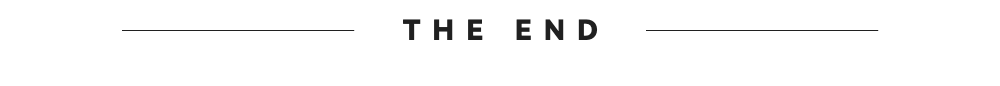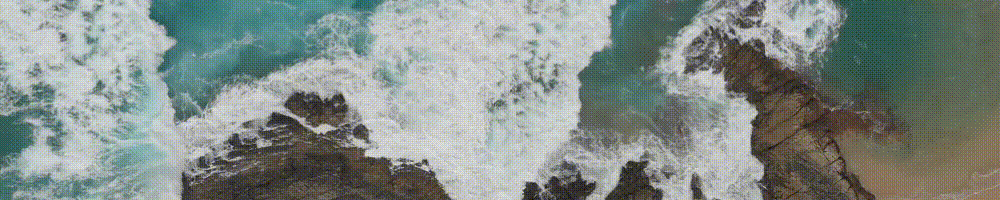
在狭窄空间之内,在有限的财政扩张资源的约束下去实施扩张,就只能把有限的财政扩张资源用在刀刃上,务求精准,重在精准,贵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文|《财经》记者 邹碧颖 实习生 王美霖
编辑|王延春
“在狭窄的空间之内,在有限的财政扩张资源的约束下去实施扩张,就只能把有限的财政扩张资源用在刀刃上,务求精准,重在精准,贵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怎么做到精准?这需要借用业界对于财政政策配置的批评之语叫做‘挤牙膏式扩张’,财政政策是不挤就不扩张,不挤就不发力。”1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第二十八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强调,2024年,甚至包括今后若干年财政的扩张就是像挤牙膏,就是要以“挤牙膏的方式”实施扩张。中国以往曾经开闸放水式的扩张,容易导致大水漫灌,挤牙膏的扩张可以避免这样的效果。不同于业界许多主张财政大幅扩张的观点,高培勇认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就像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一样,价格无论怎么波动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这是基准,中国的财政赤字率也应当围绕着3%而上下波动。此外,国债的规模不是问题,有多大的财政规模占GDP的多大比重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债务的利息负担,因为国债总是借新还旧,无限循环下去,但是利息是躲不开绕不过的紧箍咒,只要是按期偿付利息,利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高培勇还强调,要推进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他指出,要撬动企业的活力,就要把企业的税费负担前移至居民的税费负担。任何税收在企业都只是中间过路,企业转嫁了渠道,或者向前转嫁消费者,或者向后转嫁给劳动力要素和原材料要素的提供者,或者最终转嫁给股东。税制改革如何让企业的税负转化为公开透明的转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目前整个税收70%是流转税,20%是企业所得税,加起来是90%的企业税负,如何进行间接税改直接税,这是需要考量的问题。“政府可以确定不移的一个改革方向就是施行真正意义的分税制,分税制不是分税收,而是分税种。”高培勇认为,政策需要变不确定为确定性。回想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分税制改革,高培勇指出,当时主要的参照系是农村改革,把分劳动成果改为分劳动资料,提前分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打下的庄稼收获的成果是归自己的,才会有今天农村的改革局面。分税制当时走的也是这样的思路,把当时的若干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预先分了地盘,才有地方之间你追我赶、竞相迸发的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今天,也要按照本来分税制的要求,进一步的完善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关系的改革。高培勇指出,财政本身可以在改革问题上充当主角。4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减税让利的财政改革撬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90年代中期,中国刚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特别提出要谋划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资本市场业界对宏观政策配置中的财政政策配置是高度期待的,总是有观点认为当下财政扩张力度不足,也存在类似的批评之声。”此次论坛上,高培勇还从六方面出发,对中国财政政策的扩张施策背后的考量进行了分析。高培勇表示,首先,任何的政策配置都是多种因素权衡的结果。在审视当前的财政政策因素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其考量不仅与历史情况有所不同,亦与其他国家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财政政策的制定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而非仅仅依赖规模效应,力求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二是前车之鉴。高培勇表示,2013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三期叠加”的表述。一期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彼时则指2008年-2010年宏观政策——对推动经济快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也留下了一系列的后遗症。因此,“总有一根弦在我们脑子里,无论如何做财政政策的配置,都要设法避免再次落入另一个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人不能在同样一个地方摔倒两次。”三是需要考虑到不可承受之重。高培勇指出,2023年,中国GDP若增长5%,经济总量则预计超过126万亿元,若以十分之一的体量撬动经济恢复,需要至少12.6万亿元的财政扩张。但2023年财政收入为20万亿元,支出为24万亿元。“能够拿出的余钱究竟是多少?还有人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疫情三年每年数万亿的降税降费,2024年我们还有多大的进一步减税降费的空间?1-11月财政部公布的财政收支状况,总体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以上,但具体到税种只有增值税是正数,其他的税种都是负数。我们在谋划2024年的财政政策扩张力度的时候,要考虑一下有多大的实力和底牌加以支撑。”高培勇说。四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关于经济风险,我们常说房地产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事实上最后的一道防线是财政风险。只要财政风险能够有效控制,前几个方面的风险不能说绝对不构成风险,但至少是有保障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持续有效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底线就是其他方面的风险,绝不能转化为财政风险,绝不能继续传递到财政风险里面去。”高培勇说。此外,高培勇指出,财政问题有两个重要参照指标,一是3%的赤字率,二是60%的债务率。中国的情况,不能简单与外国相比。1958年-1979年,中国20年期间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短短40多年的时间,债务率变为50%多,这是40年累计的结果,其他国家有100%,甚至200%,中国现在的债务率不算高,还有很大的空间。此外,提及赤字率,还要注意中国的财政赤字有名义财政赤字和实际财政赤字之别。财务部谈国债用“法定债务”,法定债务包括非法律债务率,法定债务率没有到60%,但如果加上非法定的债务就是另外一回事。五是解决信心和预期问题。高培勇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三稳”,即稳预期、稳就业、稳增长,凸显了信心和预期问题的核心地位。中国经济面临的需求和投资问题是表象,实质是信心和预期问题。“我们明白对症下药的重要性,同时也清楚不恰当的干预可能带来的无效结果。因此,对于财政政策在解决预期和信心问题上的作用,我们不应抱有过高的期望。”高培勇说。“对于2024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经济的恢复进程,一定要潜下心来深入思考,中国的经济、中国的资本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高培勇表示,绝不能简单搬用以往应动周期性波动的老思路、老套路、老做法,应该在此基础上拿出契合当下经济的实情,资本市场的实情,并且务实管用的对策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