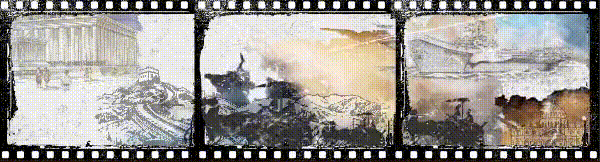

《马可·波罗行纪》(下文简称《行纪》)问世至今已有七百余年,与这位传奇的欧洲商人、旅行家有关的历史真相,连同他为世人带来的东方想象一起,逐渐被历史的长河冲淡了纹理,让今天的读者颇有一种雾里看花之感。
《行纪》详细记录了元代中国的政治事件、物产风俗,史料价值不言而喻。然而,对《行纪》真实性的怀疑,自它成书就已有之。到19世纪,已经有人利用马可·波罗没有在《行纪》中提及长城、茶、筷子等中国的标志性符号这一点,对他是否到过中国提出质疑。
马可·波罗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随他的父亲尼柯罗、叔叔马菲奥长途跋涉来到中国,于1275年在上都觐见忽必烈汗。马可·波罗自述其掌握多种语言,被大汗委以重任。后来,蒙古伊利汗国的阿鲁浑汗派遣使臣到元廷求婚,马可·波罗一家在护送新娘阔阔真去往伊利汗国后返回家乡。他们从泉州港离开中国,经苏门答腊、霍尔木兹,在波斯上岸,完成护送任务后辗转回到威尼斯。不久后,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战败被俘。在热那亚狱中,他的狱友鲁思梯切罗(Rustichello)将马可·波罗口述的亲身经历写作成书,这便是成书于1298年的《马可·波罗行纪》。《行纪》中包含了大量以波斯语发音方式拼写的中国地名,包括Chemeinfu(开平府,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Giogiu(涿州)等等。如《行纪》中对于福州有这样的表述:“从行在国最后之信州(Cinguy)城发足,则入福州(Fuguy) 国境,由是骑行六日,经行美丽城村,其间食粮及带毛带羽之野味甚饶。亦见有虎不少,虎躯大而甚强。”福州史上并无福州国之称呼,此处福州国应为福建的范围。 由于马可·波罗对提及的各类专名(如地名、官名、事物名称等)是使用波斯语译写,因此有人认为《行纪》是一部依赖波斯语材料编纂的伪行纪。对此,需要关注到元朝作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所具备的包容特性。在元代人口中,除蒙古人、汉人、女真人、契丹人等之外,还有大量色目人,波斯语被很多色目人广泛运用。对于马可·波罗这样一位来自欧洲的外国人来说,选择自己最为习惯的一门语言对各类专名进行表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刻有黄金国宫殿入口的插图——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想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对比发现,马可·波罗的记载与诸如《史集》(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主编)等波斯语史料相吻合。很多学者也通过语言学知识推断,马可·波罗可能并不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擅长汉语和蒙古语。例如,他曾在记载元初名臣伯颜时,提到他传说有“一百只眼”,这显然是不懂蒙古语的马可·波罗将“伯颜”与汉语“百眼”强行联动的“谐音梗”,被传录到书中。可见他未必真的“熟习鞑靼的风俗语言,以及他们的书法……精练至不可思议。”这也是他在专名的译写上没有采用这两种语言的原因之一。 因《行纪》中没有提及一些具有强烈中国文化符号的事物,如汉字、印刷技术、长城、茶、筷子等,有人质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真实性。这种观点站得住脚吗?事实上,对常识的疏漏,有时往往更能够证明记载的真实性。以不成比例的个案来反对书中大量真实的记载是不具备说服力的。如马可·波罗准确且细致地再现了蒙古社会的特殊习俗、忽必烈个人的性格、元朝蓬勃发展的经济情况、元朝各族群之间的关系等。而载有这些内容的其他史书,或是成书于马可·波罗离开中国之后,或不是以马可·波罗的身份根本无法接触到的,这些细腻的记载只能来自他的亲身观察。▲(元)朱玉《太平风会图》(局部),展示了元朝的市井风情。现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官网微信) 关于这一点,最具有说服力和代表性的案例便是马可·波罗在护送阔阔真前往伊利汗国时,对几位使者的记载。书中写道,伊利汗国阿鲁浑汗派遣到元朝求亲的使者有三位,分别是Oulatai(兀鲁䚟)、Apousca(阿必是呵)和Coja(火者)。“三人至大汗所,陈明来意。大汗待之优渥,召卜鲁罕族女名阔阔真(Cogatra)者来前。此女年十七岁,颇娇丽,大汗以示三使者,三使者喜,愿奉之归国。”历史学家杨志玖在元代政书《经世大典·站赤》中发现一条史料,恰好记载了这三位使者的名字,均与《行纪》所载完全吻合。在当时,马可·波罗能够准确无误地写出三位使者的名字,只能说明他曾真实地参与到与三位使者共同护送阔阔真的任务中。更为重要的是,马可·波罗记载三位使者中的两位在长途跋涉中不幸死去,只有火者活了下来。而《史集》主编拉施特在讲述这件事时,也只提到了火者一人的名字。此外,《行纪》是一部私人回忆,在内容上必然会有个人的偏好和选择。马可·波罗是一位商人,因此他的行纪包含了大量元代商业、物产和税收等内容。在介绍元大都(今北京)时,他对这座城市的商业活动和物资流通情况颇费笔墨:“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此汗八里(Cambaluc,即大都)大城之周围,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元朝至元通行宝钞。(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行纪》第二卷《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一章,十分详尽且精准地介绍了元代纸币的制造、使用和流通制度,是研究元代货币制度的重要参考史料。可见,比起文化领域内的议题,他对经济话题更感兴趣,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他对部分文化内容的忽视。马可·波罗显然无法将他在元朝所见的所有事物都一五一十地囊括到他的口述中去,正如他临终前所言,他还没有讲出他真正看到的一半。事实上,关于马可·波罗来华真实性问题,诸多海内外学者都给出了专业的学术回应,即马可·波罗一定来过中国。▲元大都城垣遗址中的马可·波罗雕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被用来质疑《行纪》真实性的几样证据中,有些并不符合元朝的实际情况。饮茶等生活习惯,未必在北方草原具有普遍性。以《行纪》中有关饮品的记载为例,马可·波罗提到:“鞑靼人饮马乳,其色类白葡萄酒,而其味佳,其名曰忽迷思(Koumiss)……”他同样提到了汉地的饮酒习惯:“契丹地方之人大多数饮一种如下所述之酒:彼等酿造米酒,置不少好香料于其中。其味之佳,非其他诸酒所可及。盖其不仅味佳,而且色清爽目。其味极浓,较他酒为易醉。”或许在马可·波罗看来,比起饮茶,不同品类的酒酿是一个更为有趣的元代中国社会切面。但不得不承认,马可·波罗或他的执笔者鲁思梯切罗爱好吹嘘。例如马可·波罗对他和他的家族参与襄阳之战(1273年发生的围城战)的记述,和他在扬州做官的经历引人生疑。因为襄阳之战结束于1273年,而根据《行纪》,波罗一家应当于1274年年底才到达华北地区,因此他们不可能参与这场战役。由于扬州是元代重要的商业中心,曾聚集着一些富有的欧洲商人家族,马可·波罗在扬州定居期间可能从事某种临时性的小官,后来被他自己或者鲁思梯切罗夸大。▲据说马可•波罗及其叔父的遗物中,有两块写有八思巴蒙古文的牌符。图为陈列在内蒙古博物院展柜中的八思巴文圣旨金牌。(图片来源:新华网)诚然,马可·波罗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或许有着爱好夸大自己才能和见闻的小毛病。同时,他有限的记忆力和理解能力也无法洞悉元代中国的一切,而这些都被自然而然地带入到《行纪》中。 时至今日,《行纪》中仍有很多谜题有待拾遗,这与元代中国的特殊性和马可·波罗的个人喜好侧重有关。马可·波罗虽然“不完美”,但他的回忆生动鲜活地向我们展示了元朝的一些历史细节,这正是《马可·波罗行纪》经历七百余年的历史,仍然熠熠生辉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