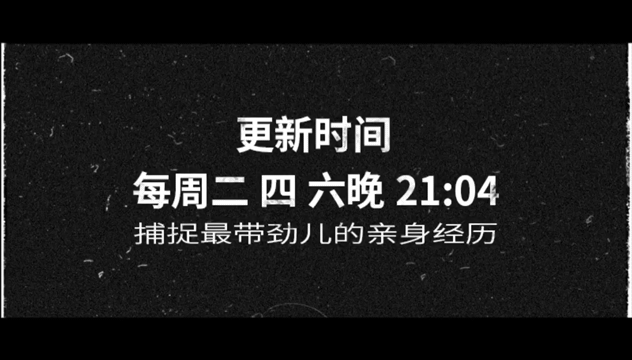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我因为点外卖被我妈训了。她看见淀粉肠上了热搜,连打了两个电话告诉我少吃外面那些没营养的。
法医苏五千劝我别跟我妈呲,她说这是你妈对你好的表现,如果真的不喜欢你,她不会说外卖没营养,而是会斥责你浪费钱。
她曾遇到一个案子,有个婆婆杀死了儿媳,招供时大喊,谁让她天天点外卖。
她本以为这就是最常见的婆媳矛盾,但现场的惨烈让她不得不思考,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
苏五千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故事:它解释了两个女人彼此仇恨的真正原因。

2022年5月初的一个傍晚,刚下班的我又接到了中心转来的警情,说“有个人正在用绳子勒另一个人的脖子”。
我坐着警车一路狂飙抵达现场,一下车却看见了一个不该见到的人——我师兄。明明半个小时前,他刚接到报警赶去那个“用刀子捅人”的现场了呀?这是一个不太急的拐弯路口,一条很长的黑色刹车痕从马路中间向路的右边延伸,尽头是一辆橘黄色的小轿车。车头撞在了路边的大树上,凹进去一个大坑,树皮被撞掉了好大一块儿,露出白色的木质部。师兄在我脑袋上拍了一巴掌,让我去戴口罩脚套,跟着他去车里看看。很快我就明白了这“乌龙”是怎么发生的——就在这辆车里,有一个人先后遇到了车祸、刀刺、勒颈,三次杀害。进一步的勘察更让我震惊:这么血腥的现场,凶手,竟然是一名女性。
钻入车厢的一瞬间,虽然戴着口罩,我还是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驾驶台、后座都泼满了鲜血,出血量大到让人怀疑一个人有没有这么多血。前风挡玻璃碎了,蛛网一样的裂痕中,大概可以看出有两个中心点:一个在右侧A柱附近,明显是A柱变形导致玻璃碎裂;而另一个中心点在玻璃上方的中间,还沾着许多毛发,应该是人脑袋从车内撞的。我又拉了拉驾驶位上只剩半截的安全带,确认它是锁死的,而副驾驶的座椅整个被从后面掀了起来,翻在驾驶台上,它的安全带也没被拉出来。说明车祸时,驾驶员应该是被安全带锁死在了座位上,而副驾驶上没人。所以玻璃上的坑,大概是后座的乘客在巨大惯性下飞出去,头撞上玻璃导致的。我用镊子拔出嵌在玻璃缝隙里的头发,发色偏黄,卷发,是个女乘客。看痕迹,车里的血好像也是她的。一般人撞这么一下肯定就废了,我正想着是不是这女的被撞晕了,然后司机又把她怎么了,后座发现的“凶器”很快颠覆了我的猜测。黑色的女士包,里面塞着几张纸币和一串家门钥匙;一条棕色豹纹丝巾;一块巴掌大小的灰色鹅卵石,上面沾有血迹;一把水果刀和一团带血的尼龙绳。绳子上缠绕着几根黑色长发,和挡风玻璃中卡住的女乘客的头发不一样。我回到车里检查。主驾的座椅调整得很靠前,这种近距离抱着方向盘开车的方式,常见于女司机。仔细一看,副驾翻起的座位下,还掉落着一个红色的女士手包,里面装着口红。所以,司机是一名黑色长发的女性,她才是被勒的那个。我见过的女性制造的恶性犯罪,受力量限制,再血腥也血腥不到哪里去,何况是两个力量较弱的女性之间,弄成这个架势,实在太罕见了。后座的女乘客虽然流了这么多血,但她反而是凶手。是她先动手、车祸再发生,还是车祸后,她顶着一头血爬回后座再勒住女司机?我一时无法确定。返回现场的派出所同事告诉了我答案。据他们说,他们赶到的时候,小车已经撞在树上,他们走近才发现车里还有两个人,坐在后座的那个正用绳子勒着驾驶座上的女人。他们吓了一跳,立刻警告那人停手下车,后座的人抬头看了他们一眼,他们才发现,那是一个老婆婆,满脸鲜血。她反应冷静得出奇,慢悠悠地在车里收拾好东西,才从后座下车。见警察掏出手铐,就主动将双手合拢,伸了过来。手铐拷上的时候,老婆婆抬头看了看西边金色的霞光,笑着说了一句:“七十换五十,值了!”

说到这里,同事都忍不住感叹了一句:“像举行某种仪式一样,搁瘆人(吓人)。”老婆婆说的七十,应该是她自己七十岁;五十则是被她勒住的那个女司机。同事打开车门的时候,女司机已经没气了,虽然送到医院,估计也救不回来。果然,我们赶到医院时,女司机已经被送到太平间。我们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尸表检查,很快决定把尸体带去解剖中心做进一步的解剖。而我则拿了相机,赶去急诊科。嫌疑人正在那里接受治疗。她身上有些伤是关系到证据链的完整的,比如勒人需要用很大的力量,那么她的双手肯定也会勒出伤痕,我作为法医也需要把这种伤痕拍照固定。走进处置室,我一眼就看到了一个一头黄色卷发的背影。医生正给她包扎头上的伤口,伤口的位置在额顶部,符合我对车玻璃裂痕的猜测。我视线往下,瞄准了自己要取证的双手,戴着手铐的双手此刻正紧紧地握在一起。现在已经五月份了,根本不用随时都戴着手套。而且她戴的是一双很普通很常见的工业手套,已经被鲜血浸染,只有手背的地方还能看见一小片白色。我亮明身份,把她的手套摘下来仔细检查,在左手套掌心的位置发现了一个破口,破口整齐,像是利器造成的。我想了想,又去看她的左手掌,果然,对应的位置也有一道创口,创缘齐整,创角锐利,此刻虽已经不再出血,皮肉还外翻着。明显是新伤,不知道是不是和死者发生了打斗。无法想象,这老婆婆是如何用已经伤得如此厉害的手,勒死了一个人。医生包扎完脑门,让开身子,我第一次直视老婆婆的脸,惊悚地发现,她的右眼里竟然插着一块玻璃。医生在旁边下着医嘱:“这只眼睛已经不行了,直接拔了就行。”然后就见他从护士手里接过一把止血钳,捏住露在外面的玻璃,速度极快地拔了出来。鲜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医生用一团纱布直接捂了上去。我没看见他有打麻药的动作,大概是没打。这位七十岁的老婆婆一下子全身紧绷,牙齿咬得咯咯响,但愣是一声没吭,只有带着手铐的双手猛地挣了一下,发出了金属的脆响。
嫌疑人的状况不宜问讯,我拍完照就从急诊科出来,却见门口围了一圈人。见多了死者家属在现场的痛哭,我本来已经不爱凑这种热闹,但这回却罕见地被吸引了——正在哭的,竟然是个男人。我从人群中钻了进去,就见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头仰面躺在地上哭嚎,不时还蹬着两条腿在地上搓。一个穿着白衬衣西装裤、带着银边眼镜的中年男人在旁边低声安慰着,还试图将老人从地上抱起来。不一会儿,中年男人的白衬衣上已经多了好几块污渍,裤子也被蹭上了泥土,显得有些狼狈。“小福啊,快带你爹去车里拾掇拾掇,一会儿公家就来问话嘞。”我看得正起劲,突然被师兄一把拎了出来,直接搡到车里。我莫名其妙地回过头,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戴上了帽子口罩,跟做贼似的。我问师兄咋的了,他悠悠地看我一眼,说这几个人认识他。那个不怕疼的老婆婆,名叫张翠苗,躺在地上耍赖的是她老伴,文质彬彬的那个是她儿子李宝福。8年前,师兄去这家出过警。师兄说,这家在村子里很有名,因为那个儿子李宝福是个体制内的医生,在那个小村子里,能考上体制内,算是特别光宗耀祖的事情。死者名叫安茹,跟李宝福是大学同学,自由恋爱,毕业后一直没有考上编制,就干脆当起了家庭主妇。看起来美好的家庭,在他们赶到的那天,只看见安茹写在床单上的一行血书:“丧尽天良,活该断子绝孙”。警方当时费了好大功夫走访,村民们要么说什么也没听到,要么就说一家人都和睦,相处得挺好。最后,是联合村委在村子里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普法教育,才取到了真实的笔录:由于安茹和李宝福结婚十来年没有孩子,婆婆张翠苗曾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骂安茹是不下蛋的鸡,害他老李家无后,害她儿子没脸等;还有很多人见过张翠苗当面责骂安茹,也有见过安茹掉眼泪的。师兄扔给我一个看傻瓜的眼神。他说他们后来审讯得知,安茹提过要离婚,但张翠苗要求她退还十万彩礼钱,还说她这么些年没生儿育女,害老李家抬不起头过日子,得赔偿他们精神抚慰金五万块。结婚这么些年,李宝福的工资卡一直在张翠苗手里,家用都是从安茹的嫁妆出,现在根本拿不出钱来。张翠苗就提出了另一套说辞,不给钱就别想离婚,以后安茹不仅要负责全家人的日常生活,还不能管自己儿子在外面找小的,直到能生出来带把的为止。安茹走不了、过不下去,在这样的绝望中,选择了最丑陋的死法。我把牙咬得咯吱咯吱响:“他们是家庭冷暴力,应该抓进去!”师兄摇摇头,说太难了。当年警方想定张翠苗一个虐待罪,但张翠苗只承认自己说过安茹,却从没打过她,村民们也没见过她打儿媳妇。家里的另外两个男人,老李是完全站在自己媳妇这边,李宝福则从头到尾都在哭,没有给出任何证据。2014年还没有把家庭内的语言暴力定为虐待罪的先例,警方想尽办法,最终也只能无罪释放。师兄作为警方的一员,对当年这家人的能闹还记忆犹新,现在是能躲就躲。
解剖中心的无影灯明亮刺眼,女人安静地躺在解剖台上。在开始解剖前,侦查的同事带回消息,这个死者名叫赵艳艳,是李宝福的第二任妻子,张翠苗的第二任儿媳。这是第二个安茹。想到这里,我甚至觉得自己作为一名警察,有些对不起她。赵艳艳今年49,身高162左右,身材有点胖,穿着橘色的毛线衣,黑色的紧身裤,一双白色的粗跟短靴,黑色的头发烫着大发卷,右侧还别着一个精致的水晶发夹,感觉是个很讲究的中年女性。此刻,她紧闭着眼,明显青紫的脸、乌青的嘴唇还有明显紫绀的指甲,球睑结膜上的针尖样出血点,都显示她死前极度缺氧,可以确认是窒息死亡。一条清晰的勒沟从死者的颈部左侧向前,通过甲状软骨上方,延伸到颈部右侧。在此周围,还有数条纵向的抓痕。为了保留颈部的痕迹,我用“Y”字型解剖术式,绕开勒痕,掀起颈部的皮肤,耐心地将颈部的肌肉一条条的分离出来,肌肉出血的位置与皮肤勒沟的位置一一对应。舌骨骨折,手指甲里还有皮肉混合着鲜血,很明显,赵艳艳死前曾极力挣扎过。但我不明白的是,她一个50岁的正值壮年的妇女,为啥会被一个70岁的老婆婆紧紧勒住脖子挣不开?随着胸部皮肤切开,我用刀片将肌肉组织沿着肋骨剔除,胸部的损伤一下子就呈现在了我的面前。自左锁骨开始,沿着左肋骨向右至右侧肋骨处,共计有13根肋骨发生了骨折。骨折线斜着向下,让我想起了安全带。这种安全带损伤在交通事故中很常见。当车辆遭受重大外力撞击的时候,安全带锁死,虽然保护了人体不至于撞上玻璃甚至飞出去,但也可能会勒伤人体,严重的就像这样,肋骨骨折。这样巨大的疼痛下,即使赵艳艳完全清醒,也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开胸完成后,我又检查了赵艳艳的头颅。隔着头发都能摸到,她头上有一个很大的头皮血肿。我想起了黑色女士包里沾血的鹅卵石,是不是张翠苗还用石头砸了她?师兄帮我固定着死者的头,我直接用开颅锯打开了她的颅腔。然后,顾不得空气中骨粉的味道,我俩同时凑近了观察。奇怪的是,颅腔里面一切正常,并没有出血。是砸得太轻没有留下痕迹,还是这个伤是早就有的?虽然已经可以确认张翠苗的勒颈行为是直接死因,但对于头上这个额外的伤痕,我也不愿放过。第二天一早,我们联系了死者家属李宝福,要向他说明尸检情况,也问问他赵艳艳头上的伤。当然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男人的妈妈弄死了他两任妻子,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一次,他还要为了母亲保持沉默吗?张翠苗又是为什么,从辱骂上升到了亲手杀死这第二个儿媳?
坐在询问室里的李宝福看起来文质彬彬,头发向后梳起,甚至抹了发蜡。我跟他说了赵艳艳尸检的情况,他点头应下,看起来没什么情绪。问到赵艳艳头上的伤,李宝福解释道,这个伤应该不是他妈妈导致的。几天前,赵艳艳曾经跟他提过头疼,他问了才知道,妻子跑去跟前夫要拆迁补偿款了,被前夫推了一下,头撞到了墙。他状似不经意地补充解释了一句:“艳儿跟我是三婚,这个‘前夫’是她头婚的那个。”他还从随身带着的公文包里面拿出了赵艳艳的CT检查报告单。我检查着报告单,日期、伤情都无误,头上的伤不是张翠苗砸的。李宝福带着这个片子,不知道是单纯的谨慎,还是在想尽办法为他妈开脱。同事在一边没好气地说:“你怎么说?还是跟以前一样,护着你妈?”李宝福并没有生气,不紧不慢地解释道,他知道八年前的事情是母亲不对,所以这次娶了赵艳艳,他的立场是很鲜明的,为了避免婆媳矛盾,直接和妻子住在县城里没回去。悲剧发生的地方是县城回老家的路上,开车的是赵艳艳,估计是母亲跑来城里找他们了,妻子送她回家。李宝福连母亲什么时候来的都不知道,也没收到妻子的消息,实在防不胜防。据李宝福说,母亲张翠苗和妻子赵艳艳之间的矛盾还是因为孩子。赵艳艳是三婚,她跟头婚的丈夫有个儿子,叫王兴。第二次结婚时,那个丈夫曾经要求她再生个孩子,她坚决不干,怕第二个孩子分走儿子的宠爱,为此宁可离婚。所以跟李宝福结婚后,她也不肯再生。李宝福是知道这个情况的,他说自己一直把赵艳艳的儿子当自己亲生的,甚至自己的钱、房子,都打算给这个孩子。对此张翠苗非常不满,经常喊着要他离婚再找个能生的。但赵艳艳不像安茹,性格泼辣,自己就能跟张翠苗骂得有来有往,不让李宝福插手。事发当天,对于婆婆的突然造访,她可能也没放在心上,没有通知丈夫。他们都没想过张翠苗会做到杀人这一步。这倒是把自己摘得够干净的。我狐疑地问他,赵艳艳不肯生,你真答应?李宝福点点头:“我自己是医生,艳儿这么大的年龄,就算能生,风险也是太大了。”他说只要赵艳艳的儿子肯认他,跟他自己生的也没区别了。这么看,他倒是个讲道理的,摊上这么个陷入执念的妈,可能他也没办法吧。后来对张翠苗的审讯也证实,杀人动机基本可以概括为为了抱孙子产生的婆媳矛盾。我没有理由再刁难李宝福,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尸检报告,通知家属来领取赵艳艳的尸体。李宝福接到通知来了,但让人意外的是,赵艳艳的亲儿子王兴也来了。这俩人谁也不让谁,都争抢着要领走赵艳艳的尸体。王兴年轻冲动,在公安院子里大吵大闹:“你妈杀了我妈,你还妄想把我妈埋你家祖坟里,这是不可能的!”我在心里很快估了一个数,按照赵艳艳的年龄,走法院大概能要到80万。不同于王兴的愤怒,李宝福显然要沉稳很多。他扶了一下自己的眼镜,慢条斯理地讲条件:“艳儿是我的合法妻子,你是艳儿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我的东西,最后都是给你的。我们还按照之前说好的弄就行。”他们之前说好啥了?不用我问,王兴立马指着李宝福的鼻子骂出来了:“放你娘的狗屁,李宝福,你还惦记着我给你当儿子呢?”“你自己不能生,就糊弄我妈,还想我改姓李,我劝你别做梦了!”我瞬间瞪大了眼睛,李宝福不能生,真的假的?他妈知道吗?他妈弄死两任儿媳,就为了个孙子,这不搞笑吗?转脸看去,李宝福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惨白,嘴唇颤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用低沉的语气说,他确实不能生育,跟安茹结婚的时候就发现了。李宝福摇了摇头:“安安如果知道了,一定会跟我离婚的。”刚才王兴说过,他妈也就是赵艳艳也是不知道的。我在心里暗暗地骂李宝福“渣男”:“那你就由着你妈逼死了安茹?”我脑子一下没转过弯来,想了又想没想明白,张翠苗从一开始就知道是自己的儿子不能生育,那她因为想抱孙子杀儿媳,这个理由根本就不成立啊?儿媳要是真给她抱个孙子回来,她才要怄死了好吧?我一脑袋问号,一直憋到张翠苗伤情稳定被移送拘留所那天,终于找到机会问她:“你的儿子不能生育是事实,你却为此杀了两个女人,值得吗?”张翠苗脸色大变,疯了一般地朝我扑来,被同事一把按住,还在嘶吼着:“不许污蔑我儿子,他没有问题,没有!”我站在原地,打量着她的脸,这不是听到陌生事实的震惊表情,而是愤怒。李宝福没有撒谎,他妈妈张翠苗真的是知情的。那么她此前招供的所谓因为想抱孙子而杀人,又有几分真几分假?张翠苗作为嫌疑人,住院的时候需要警察尤其是同性别的警察24小时看护,公安局里女警不多,我之前跟她一块待过几次。自从有一回我把凑单的奶茶送给她后,她甚至会跟我闲聊几句。喝奶茶那次,她的开场白是:“这什么东西,没有我儿子买的好喝。”接着,突然紧紧盯住了我:“你一定有见到过我儿子吧,是不是特别帅!”诚然,李宝福身材管理得当,并没有谢顶和啤酒肚,加上穿着白衬衣黑西裤,并没有中年大叔的油腻感,但再怎样也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了,和帅是不沾边的。可惜张翠苗似乎不觉得,说起她的儿子,她的脸上就会呈现出特别骄傲的神色,眼睛里也满是光彩。她特别炫耀儿子跟她亲,说儿子上大学放假回来,也会粘着跟她一个床上睡,给她讲自己在学校的各种趣事儿,会给她带礼物,发夹,丝巾,护肤品。她还炫耀自己儿子的能干,在单位是科室主任,病人给他送了好多面锦旗……我说顺着她说是啊,其实现在很多优秀的年轻人都选择丁克,一辈子没有孩子的,你儿子已经很优秀了,你不用这么着急的。张翠苗用仅剩的一只眼睛对我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说:“你个小屁孩儿啥也不懂,没有孩子,是很难活下去的。”
张翠苗说,她的儿子李宝福“来得很晚”。当时结婚有好几年都没孩子,公婆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村里人整天闲言碎语。唯一不催促她的人是丈夫。她丈夫是个老好人,总是安慰她不用着急,两人好好挣钱过日子就好了。夫妻二人相互扶持,硬生生成了村子里第一个住上二层小楼的人家。可有一年,亲戚突然故作大方地说可以过继一个儿子给他们,条件是以后家产都必须留给这个孩子。这就是明摆着吃绝户,看不起他们,丈夫发了好大脾气。再后来,丈夫开始喝酒,回家也越来越晚,有时会彻夜不归。张翠苗知道,丈夫是心里不好受,村里人除了议论她,也风传是她丈夫“不行”。但丈夫从没跟她提过离婚,更没打过她骂过她,这让她更加心疼自责。在张翠苗的记忆里,一切的转折都源于儿子李宝福的降生。一次赶集,她无意中遇到了一个走方游医,给她开了一个方子,她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喝了,却真的怀孕了。李宝福出生以后,全家的日子都在往好走。儿子成绩一直很好,乖巧听话,一路考学成了小村庄里第一个医学生、第一个公职医生,接着又娶回了一个读过大学的女朋友。我不知道张翠苗当时真正的反应是什么,是不能接受自己精心培育的孩子竟然有瑕疵,还是担心自己曾经受的流言蜚语会同样伤害儿子。但总之,她选择了把脏水泼到儿媳身上。就像当年自己的婆婆一样,张翠苗对安茹极尽羞辱。安茹自杀后,她对警察说了一句话:“哪个女人不被村里的长舌妇议论,就她矫情寻死。”也许安茹死后,张翠苗也是后悔的,据说她拼命给儿子找新儿媳,却很少有女人愿意来见面。更关键的是,李宝福自己也十分抗拒,甚至越来越少回老家,一个人住在镇子里。这也是自小乖巧的儿子第一次这么忤逆她。这样僵持了四五年,李宝福突然带回了赵艳艳,说要结婚。最开始张翠苗肯定是开心的,还主动给他们房间换上了大红色的四件套,让他们搬回家来住。但很快,婆媳俩又斗上了。在张翠苗眼里,赵艳艳的罪状数都数不完:骄奢淫逸,给她儿子吹枕边风,关键是不生孩子,摆明了就是要那个外姓孩子吃他老李家的绝户。这成了张翠苗最终杀人的动机。事发当天,张翠苗是来县城给儿子送薄被子的,因为天气热了。结果一打开门,发现赵艳艳穿着睡衣,披着头发,明显懒觉睡到了中午。看她来了,赵艳艳呵欠连天地给楼下的饭馆打了电话,让老板送三个菜并两碗大米饭上来。“一看就是天天这么干,电话里熟得很,都不用报菜名,就说老规矩,那老板就啥都知道了。”张翠苗说自己儿子起早贪黑地上班挣钱,而赵艳艳却每天在家里甚也不干,就吃她儿子的用她儿子的,凭什么?她跟赵艳艳吵了起来,赵艳艳让她少管闲事,还给她听了一段录音,说你儿子都说了,家里房子拆迁后,要把最大的那个给我儿子结婚用。这段录音,我们后来也确实在赵艳艳手机中找到了,录音里赵艳艳声音特别嗲,带着哭腔抱怨前夫不给她房子,李宝福一句一句哄,最后确实也说了把房子给王兴。对于赵艳艳,我们也有过不少猜测,这个女人第二次离婚后,单身了近十年,直到儿子王兴刚满20岁,她突然跟李宝福结婚了。结合她专门留下这种录音的行为,就算是我们这样的外人,也很难不怀疑,她就是为了给儿子挣彩礼来的。而听到录音的张翠苗当然大怒,“一听就是在床上偷偷录的,根本就是个不知廉耻的贱人。”俩人吵了一下午,赵艳艳性格泼辣,丝毫不占下风。最后张翠苗说自己不想再见到赵艳艳,让赵艳艳开车送自己回去。趁赵艳艳进里屋换衣服的时间,张翠苗在客厅找了一个牛奶袋子,将捆被子的绳子取下来,带上了手套,又将桌上果盘里的水果刀抓过来也塞了进去。
夕阳下,赵艳艳一边开着车,一边仍然在语言奚落张翠苗。张翠苗不搭理她,全神贯注地看着窗外的景色。“我专门选了路过祖宗坟地的时候动手,就为了让祖宗们都看着。”车开到张翠苗计划的地方,张翠苗戴上了事先准备好的白手套,举起水果刀割向赵艳艳的脖子。赵艳艳从后视镜里看见了,伸手来挡,同时紧张之下方向盘一转,车子就撞在了大树上。张翠苗飞出去撞在了前风挡玻璃上,玻璃扎进了眼睛、划伤了手。赵艳艳则被安全带勒断肋骨,晕了过去。张翠苗好像感觉不到痛,随手摸了一把头上流下来的血,就爬回后座,看到从袋子里掉出来的尼龙绳,拿起来就绕上了赵艳艳的脖子。中途赵艳艳醒过,抬手抠抓她,拼命挣扎,她就更加用力。不知道过了多久,张翠苗听到耳边传来了一声怒喝:“我们是警察,立刻停手下车!”这时候,她才发现,赵艳艳已经脑袋歪在一边,不动了。张翠苗说,她还使劲拽了赵艳艳的头发,见赵艳艳没反应,确定真的死了,她才将绳子等物件收拾齐整放好才下车,向着李家祖坟磕了一个头,然后被警察带走。我还记得医院里看到医生给张翠苗拔碎玻璃那瞬间给我的震撼,眼睛里扎着玻璃、手上豁开口子,还能杀人,她的杀意超过了求生本能。其实不管赵艳艳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老李家都是会“绝户”的。我想张翠苗最不能容忍的,是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占便宜”——即使她儿子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张翠苗入狱后,我们通知李宝福领取母亲张翠苗的衣物,李宝福依旧是那副彬彬有礼的模样,签了字就拿着大包向外走去。赵艳艳的尸体最终由她的儿子王兴领走。在他们走之前,李宝福坚持要见赵艳艳一面。他先跑到卫生间,把自己好好拾掇了一番,然后才跟着我们进了太平间。在冰冷的停尸间里,他从随身带着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顶崭新的黑色披肩假发,戴在了赵艳艳的头上,又拿出一条红色的丝巾,围在了赵艳艳的脖子上,还细心地系了个蝴蝶结。
一切弄好后,他直起身,反复地对我们说着:“麻烦了,添麻烦了。”我漫不经心地应答着,无意间瞟到被他打扮后的赵艳艳,这个样子,好眼熟,像谁呢?——像安茹!我突然明白了很多事,一瞬间,我对这个男人只有更深的厌恶。我后来才发现,李宝福所谓的“把王兴当成自己儿子”,其实有很大水分。王兴没有正经工作,二十多岁没有谈婚论嫁,但李宝福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只是一直在给王兴画饼,或者说威胁:“只要你改姓,我的就是你的”。王兴最终也没有改姓。赵艳艳死后,李宝福作为张翠苗的家属,向王兴赔偿了60万加一套房子。王兴没有如他所愿留在李家,而是带着那笔钱离开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希望他走得远远的,再也不用回到那个“家”,那个小镇。
看完这个故事,我问苏五千,“绝户”这件事在你们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她打了个比方,有亲生孩子但孩子不孝孤独终老,和没有后代但小富即安,在他们那里,可能大多数人宁愿选择前者。50年前,“绝户”会让张翠苗寝食难安,挣多少钱也过不好日子;三四年前,李宝福会为了“绝户”处心积虑地逼一个孩子改姓;而现在,一个年轻人根本不理解“绝户”意味着什么,他只会在乎爱他的人、他自己的未来。
插图:大五花
本篇9922字
阅读时长约28分钟
如果你想阅读更多【苏五千】的故事,可以点击下面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