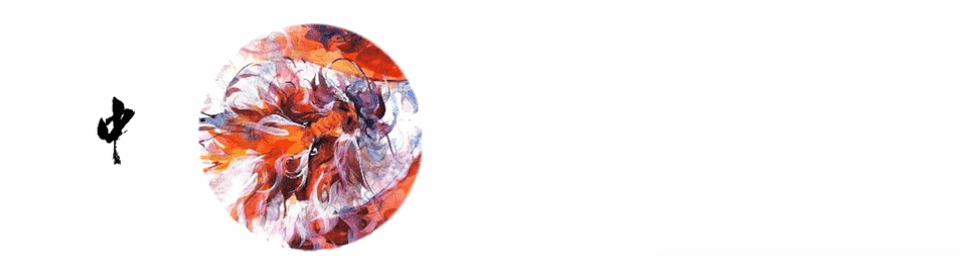

继MBTI16型人格测试之后,网络又兴起了浓人淡人的新人设。虽然这两者没有官方解释,但顾名思义,所谓浓人,是指情绪浓度高,常以丰沛的情感对待感兴趣的人事物,外显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淡人则是情绪稳定、处事平淡,具有泰山崩于前而不色变的镇静。
现代人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看淡名利,弱化物欲,只愿在自己的世界里淡淡地活着,而相对来说,倒是很多古人更为潇洒恣意,挥斥方遒地度过一生。

《西园雅集图》(局部)明 程仲坚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提及金圣叹这个名字时,或许很多人想到他评点的《水浒传》,想到他是明末清初苏州吴县的文学家,想到他对《西厢记》的情有独钟,而可能会忽略一个他性格上的特质,所谓“人如其名”,能取名叫“圣叹”,要么大才,要么出尘,要么傲慢,要么荒诞,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浓人”。
从金圣叹的早年经历便可看出,他是个不折不扣特立独行的乐天派。金圣叹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少年时期家境尚可,有田产家财。并且年少早慧,十岁入乡塾,年纪很小就考中秀才,顾公燮编《丹午笔记》中载:“金圣叹……为人倜傥不群,少补长邑诸生,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次年科试,顶张人瑞就童子试,拔第一,补入吴庠。”但他自命不凡,觉得夫子所授四书五经索然无味,儒学传统义理只重教化,单调无趣。金圣叹原名采,字若采相传金圣叹读《论语》时,读到曾点因崇尚自由,不入仕途而为孔圣人赞叹,顿觉自己也会得到孔圣如此赞扬,自更名为“圣叹”,还自称“孔子身后第一人”,不可谓之不狂妄。他少年读书却对书籍极为挑剔,从小接触佛道却依然有入世之思,性格上率性孤高,玩世不恭,万千学子奉若神明极为重视的科举考试,在他眼里也仿佛游乐场一般。相传他首次参加科考,面对“吾岂匏瓜也哉,焉能击而不食”的试题,竟在试卷上绘了一个光头和尚和一把剃刀,自称“此亦匏瓜之意形也”,震怒考官。落第后依然狂放不羁,再次参加科考时,对“吾四十而不动心”的题目,他在试卷上连写三十九个“动心”,以“孟子曰四十不动心,则三十九岁之前必动心矣”这样的游戏心态来应答,对待科举举重若轻,绝不愿敛心收性,曲意逢迎。试文不对程法,金圣叹游戏科场的后果,就是屡遭黜革,入仕无望。即便如此他也不愿循规蹈矩,还说“为儿时,自负大才,不胜侘傺。恰似自古迄今,止我一人是大才,止我一人是独沉屈者。”始终狂放不羁,清代王应奎所著《柳南随笔》中称他“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仕途无望,他开始“装神弄鬼”,从事传统文人所轻的怪力乱神之事。扶乩是古代民间信仰的一种占卜方法,又叫做“扶箕”“扶鸾”,需要有人被鬼神附身,借人之口传达鬼神的想法。金圣叹自称佛教天台宗祖师智顗弟子转世化身,托名“泐庵”法师,扶乩降灵,扮演被神灵附身的角色,并借神灵之口,将自己的佛道思想灌注在文章之中。他与戴云叶、魏良辅等友人频繁参与降神活动。此后几年,他文名渐盛,狂放之行亦渐多,甚至还受邀到叶绍袁、钱谦益、姚希孟、戴汝义等士大夫家中扶乩,借以表现自己的诗才与佛学修养。浓人和淡人调动心理能量的方式不同,淡人喜欢以平淡度日的方式储存内心的能量,而浓人势必将经历集中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上,浓浓地表达好恶。壮年时期的金圣叹开始著文章以自娱。初读《水浒传》,他便一下子入了迷,达到“无晨无夜不在怀抱”的状态。“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喜欢什么就要告诉全天下,他在《水浒传》第十四回总评中写到:“嗟呼!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将无从实现的功名之志转移到文学评点之上,成为他文学和审美的精神寄托。金圣叹强调人物描写必须合乎人情,使读者感到亲切可信,因而主张用“极近人之笔”写出“极骇人之事”,既遵循古代文学审美传统,又发展出独到的文学评点之见解,在评点时注重人物心理特征和主观动机等特点,分析人物个性中的非伦理因素,将人物个性论推向高潮,成为那个时代文学评论的先驱。甚至后来的脂砚斋评《红楼梦》也受到金圣叹的影响,脂批中列举的一些写作技巧,如“烘云托月”“横云断岭”“草蛇灰线”等法,也都来源于金圣叹批《水浒传》。同时拥有天赋和热情的金圣叹在文学批评领域造诣惊人,灌濯后世,曹雪芹、李渔等文人皆受其影响。近代历史大家钱穆也曾表示是在金圣叹批《水浒传》中学到了读书方法,林语堂赞他为“十七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郑振铎甚至发出惊叹,言“金氏的威力真可谓伟大无匹!”这时的金圣叹醉心佛道,深知人生无常,浮生虚妄。和青年时期的他相比,壮年的金圣叹已忘怀得失,专注文学。他将《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水浒传》《西厢记》并称“六才子书”,极为推崇。顺治十三年(1656年),金圣叹完成了《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评点,以“贯华堂”名义刊行,这部书得到了同时代的戏剧理论大师李渔的高度评价。他坚持“文章的最高典范是精严”,首创以禅理点评戏曲的方法,将小说戏曲提高到与诗词文章的同等地位。情绪浓度高是浓人的一大特性,自然就会在很多事情上同仇敌忾,以更为鲜明的情绪表达喜怒。金圣叹曾言:“吾常言读书之乐,莫过于替人担忧。”虽未入仕途,他始终保持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同理心。他善恶分明,心忧百姓,正因如此性格,才使他在哭庙案中表现出嫉恶如仇的态度。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二月,新任吴令任维初以重刑催逼钱粮,上任之初就宣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动用严刑催逼拖欠。还监守自盗,粜卖常平仓米三千石,导致民怨沸腾。金圣叹见不得此等酷吏搜刮膏脂为害一方,为此写下一篇题为《十弗见》的文章,百般讥讽任维初。翌年二月,顺治帝哀诏至苏州,抚按道臣及府县官吏缙绅等百余人至府堂之上哭泣。已经年过半百的金圣叹不但参与撰写哭庙告文,还在哭庙当天,积极鼓动友人同赴文庙,又前往苏州府衙,上书江苏巡抚朱国治,鸣钟伐鼓,跪进揭帖,要求罢免任维初,跟随者竟达千人有余。奈何巡抚朱国治与任维初颇有私交,一心为其开脱,捏造“震惊先帝之灵、目无朝廷、鸣钟伐鼓、匿名揭帖”等罪名,将金圣叹等人逮捕,严刑拷问,最终以叛逆罪判处斩首。哭庙案爆发于江南民众长期遭受重税盘剥后的社会环境,清廷也有意借此案威慑镇压江南士族,一代怪杰最终竟以如此吊诡荒诞的方式走向生命的终结。晚年的金圣叹曾在写给友人嵇永仁的信中说到:“用是不计荒鄙,意欲尽取狂臆所曾及者,辄将不复拣择,与天下之人一作倾倒。此岂有所觊觎于其间?夫亦不甘便就湮灭,因含泪而姑出于此也。”作为离经叛道的非典型性文人,金圣叹在哭庙案中的表现成为他倜傥不羁、至诚至善的明证,同时也是他几十年治经学道、援佛释易的外显。虽然轰动一时的哭庙案直接导致了他生命的终结,但至死他都是顺从自己、至纯至真、性情浓烈之人。他求同存异地吸收儒释道之精髓,以至善之本心、放诞之言行坚守着内心的义理。有人寒窗苦读最终一朝提名,得以逆天改命走上仕途;有人终生应考郁郁不得志,被命运的颓败笼罩终身。而金圣叹似乎天生就没有悲戚的血液,惯行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内心秩序。他是奇才、狂才,也是怪才,他飘零且荒诞的结局让人为之扼腕叹息。他自负才智,一生不平顺,却始终精彩,始终遵从自心激荡的情感,以超拔的生命力量对抗命运的猛烈风暴,以倜傥不羁的人格走过独特而不朽的一生。参考资料:
《金圣叹传》陈洪,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金圣叹》吴正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金圣叹评点“六才子书”》《解放日报》,2020年4月
《十人九不知,金圣叹原来这么牛! 》哲学诗话,2017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