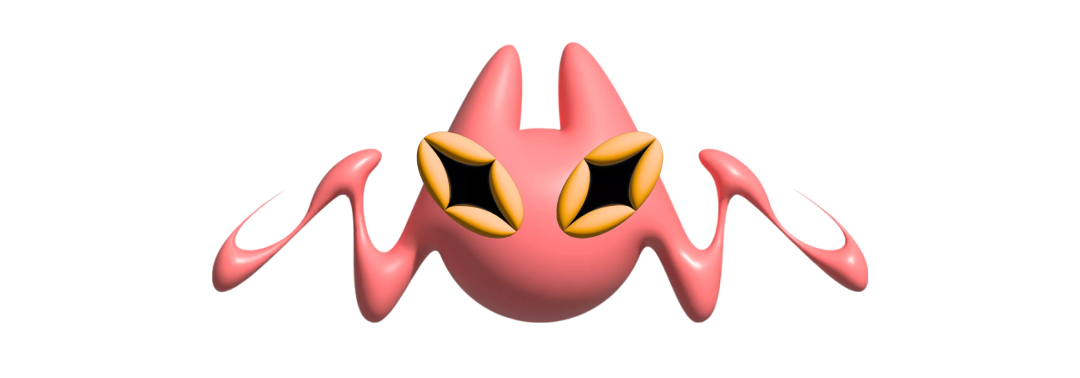“梦女”,一个衍生自日本 ACGN 文化名词 “夢女子”(ユメジョシ)的词汇,niconico 大百科将其释义为 “男性キャラクターに夢中になっている女性のこと”,也就是所谓 “沉迷于男性角色的女性”。说到梦女会想到什么呢 —— 在橙光网站沉迷过的某十二人男团明星立绘恋爱游戏,为恋与制作人男主生贺而包下 CBD 的 LED 大屏,漫展上 cos 五条悟被万人排队追捧叫老公的 coser 卡琳娜......我梦故我在。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 TA 们的梦,每一个千变万化的梦境底层,都是被压抑被干涸,无法用言语直抒胸臆的隐秘欲望。既然是 “沉迷于男性角色的女性”,梦女文学中的 “我” ,自然总是在和一个或者很多个男性,纯情或者色情地相恋着(故此,总会有人混淆了 “梦女” 和 “女友粉” 两个群体)。
但在 “梦女文学” 的边缘,有人却开始书写 “我” 与女艺人、女性角色的故事。比起异性恋叙事里迅速掉入 dokidoki 恋爱剧情的节奏,“我” 和 “她” 的相处更像小众文艺片,曲折委婉,不直白说爱意,只流动一点亲密的暧昧。
来自@许蛮蛮
博主@许蛮蛮已经在小红书写了40余篇这样的梦女文,一开始只是随意写作,后来渐渐发现,调动她写作想象力的,都是女性。同样地,为她贡献多达32.2万点赞与收藏的也是女性。也许她们自己也未想到,原来心中微妙流灿的情感版图还缺了这样一角。不在异性恋框架中,甚至不谈恋爱,在梦女这个小众框架下,许蛮蛮无意间撕开了一个汹涌的女性情感出口。这种去恋爱/去异性恋趋势,实际上也是情爱想象大潮中女性觉醒的一个小小缩影。珍妮斯·A. 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Reading the Romance:Women,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浪漫小说是一种父权制的驯化,它以甜蜜的情节为无法在异性恋关系中获得满足的女性提供了一种幻想性解决策略,以使她们满足于现行的父权制婚姻框架中。浪漫小说的底层逻辑,是从不将男人的冷酷无情和虐女行为归因于他们的薄情寡义、争强好胜或野心勃勃,而是在女主角的努力下,一个浪子总是会露出他一往情深、满腔柔情、忠贞不渝的 “好男人” 本质来。如果做不到,那只能说明女性本身不是一个完美的妻子或 “母亲”(无独有偶,启蒙大陆言情想象的琼瑶、席绢、亦舒等港台言情女作家笔下,“白莲花” 般纯洁无害的女主角也总能以其美丽的外表、善良坚韧的内心吸引男主角的目光)。但很快读者就厌倦了 “白莲花” 在情爱关系的被动地位,也不再相信靠 “傻白甜” 就能俘获男主角芳心,于是崛起了一批拥有百般技能的全能型 “玛丽苏” 女主角,金手指式的穿越小说因此成为热潮。当全能玛丽苏热潮褪去,一个值得注意的转折性变化出现了。现今流行小说里备受青睐的热门品类 —— “种田文” ——直接跳脱出了两性/浪漫爱框架。女主角不再为男女情爱伤春悲秋,也不在后宫中步步为营,而是在一宅一院中经营自己的小生活,只想着 “衣食不缺,有空闲时间学点琴棋书画陶冶情操,做点感兴趣的小手工,看看书,吃吃美食,闲了出门看看风景,有三两手帕至交,偶尔可以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八八卦”(《平凡的清穿日子》)。情爱的消逝是一种时代症候。我们不再相信 soulmate 式的经典爱情叙事。这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必然的觉醒,是不再 “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小说的流行趋势显示了女性大众对 “情感” 想象和 “自我” 期许的流变,而这也镜像般地体现在了不以男性为梦主的新型梦女身上。正如许蛮蛮这样描述她笔下的梦女文学:“不只是性缘的。她可以是鬼魅、同学、陌生人、城市里随处可见的流浪猫,以及家里的表姐。”
来自@许蛮蛮
非异性恋叙事的 “非典型梦女” 书写中,除了梦主性别的改变,另一个主要的特征是梦主与 “我” 之间占比和地位的改变。
在异性恋梦女或乙女作品中,“我” 就像一个隐形摄影机,性格扁平,便于代入,是衬托呈现男主魅力的放大镜。但在女明星梦女文学里 ,“我” 和梦主的 “她” 之间的关系则类似于女性成长叙事中的 “镜像结构”。那个令 “我” 做梦的 “她” 虽然是女明星,但也不是。她是我的同学,我的同桌,我的邻居,我在大城市上班的表姐,和我住同一个出租屋的室友。故事大多是过去式,在某个时刻,“我” 想起那些和她共同度过的,并非岁月,甚至谈不上时光,只是一些散落的记忆碎片。写马思纯:“某次数学老师拿着一刀卷子走进教室,我明显地感受到了她身上的肌肉收紧。”写蒋依依:“只是当世界的一切都还草木未明的时候,蒋依依就已经学会了如何表演夸张的诗朗诵,控制微笑的幅度,把端正的字体努力挤在小小的作文格里,排比句写得比梦还要长。”写周雨彤:“暑假过了一半,我妈打电话给周姐,让她好好看着我做题,多教育教育我。周姐满口答应,挂了电话就带我逛街。”写孔雪儿:“孔雪儿用她从老家带来的卡片机自拍,并把我和她的照片设为手机壁纸。背景是布满水渍的墙面,各种韩国艺人的海报,墙角的塑料水盆,孔雪儿花哨的连衣裙与刺绣牛仔裤,我的烟灰缸。”故事大多发生在 “她” 走向星光熠熠之前,在混沌生长的青春或者偏安一隅的时间缝隙里,两个女孩的彼此触摸。
少女之间的 “同性依恋” 在少女成长叙事中并不少见。《七月与安生》中的七月与安生,《左耳》中的李珥和黎吧啦,《少女哪吒》中的李小璐和王晓冰......女性总是先与女性接触来建立关系,而男性的闯入则往往造成一种断裂。精神分析学认为,人最开始都是通过女性(即母亲)来确立自己的性别身份。美国社会学家南希·乔德罗(Nancy Julia Chodorow)在弗洛伊德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女性在婴幼儿早期与母亲关系紧密,父亲在情感抚慰上缺席,这会引发女孩发育过程中的 “前俄狄浦斯状态”。这种对母亲的绝对依恋,使女孩比男孩更容易有双性恋倾向。而在现实的成长记忆里,我们确实曾经拥有一个不分彼此的女友。她的教室座位在你附近,会牵手去厕所,在差不多的年纪月经初潮,偷偷问对方有没有开始穿棉布的小背心。学校发新校服时,你们兴奋又不安地看着对方,猜想这件衣服在自己身上的模样。从母亲到女友,与其说女性的天性是在 “追求生命中唯一的浪漫之爱”,不如说是在同性身上寻找和投射镜像认同。这种隐秘情结多么近似梦女的燃料。这可以解释粉丝对卡琳娜疯狂的爱,在她的身上投射 “美强惨” 又渴望拯救她;也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爱嗑袁立与李红,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梦女文学;我们说 “东亚女都应该有一个堂姐”,我们向往那个叛逆的 “不婚主义小姨”,我们如此沉浸式地理解 “天才女友”......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可以让我们相互触碰,相互投影,为其沉迷的镜像投影。
来自@许蛮蛮《成为陈都灵,是我少女时期的一种英雄主义》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新型梦女:当女性意识觉醒,我们的生命成长中最关切的不再是异性情爱,而是共享同一类主体经验的其他女性。后结构主义视阈的镜像:“她是我全部心的投影”
相较于姐妹、堂姐、小姨和班上那个会弹钢琴的漂亮女孩,女艺人是更加遥远的投射。杰姬·斯泰西在对女性观众的人种志学研究《明星凝视:好莱坞电影和女性观众》(Star Gazing: Hollywood Cinema and Female Spectatorship)中,通过对数百名影迷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女性观众与好莱坞女星建立认同的不同实践和幻想。斯泰西认为,观众和明星之间的关系,都是有关 “自我” 和 “理想” 之间的互相作用。观众可以说是与她的银幕偶像 “相恋”,对偶像的爱同时表达着同性情欲快感,和 “想要变得更像那个偶像” 的欲望。而与女艺人展开的梦女文学,则超越了粉丝与偶像的二元权力/互动关系,已然是一种后结构主义叙事:她者甚至已经不再真实存在,而只是由自我制造出来的、用以认知自我的镜像装置。将镜像认同为自我,让自我迷恋于镜像,并将她者投射为理想自我,于是便有了 “成为陈都灵是我少女时期的英雄主义”。
当我们用无限美好的词汇去勾勒 “她” 身上的美好光晕,那正是我们所向往达到的理想。当我们原宥 “她” 的笨拙脆弱,也正是拥抱我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和动荡。她恋即自恋,梦女亦梦己。跳出异性恋框架的梦女文学,其探索不止局限于女性的亲密关系和姐妹情谊,还是一种进行自我探寻和自我认同的途径。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叙事是以 “女星” 为公共符号,作者和读者与陈都灵们的距离是相等的,每个人都可以不被束缚在叙述者 “我” 的视角中,而可自由代入于 “我” 和作为理想投射的 “她” 之间滑动。我们共享着 “我” 的焦虑、软弱与动摇,也被 “她” 的自由、浪漫与坚定所照耀。那些幻想出来的 “她” 和 “我”,也在阅读中被确证为真实的血肉,我们共同制造了作为 “缪斯” 的她,也拥抱了我们身上美如 “缪斯” 的部分。此刻的你我,因为共享同一段记忆而融化在一起,成为一个微小的女性共同体。感谢@许蛮蛮采访交流
参 考 阅 读
[1](美)珍妮斯.A.拉德威著,胡淑陈译.阅读浪漫小说[M].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2]白惠元.哪吒之死:镜像、幻想与缝合——近年中国少女电影的文化症候[J].文艺研究,2017(10):25-34.
[3]储卉娟. 说书人与梦工厂[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4]姜悦."玛丽苏""中产梦"与"穿越热"——对"女性向"网络小说的一种考察[J].文艺争鸣,2017(10):16-22.
[5]邵燕君. 网络文学经典解读[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6]陶东风. 粉丝文化读本[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