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图▲立即了解

如果把中年比作一个避无可避、遍布危机的沼泽,那么焦虑就是其中四处弥漫的迷雾。稍有不慎,我们便会深陷其中,难以找到前进的道路。如果把中年比作一片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那么焦虑就是扑面而来的庞大冰山。当我们行驶其中,我们要如何才能避免成为沉没的泰坦尼克?强烈的焦虑感裹挟了中年人。对于焦虑,我们究竟要如何应对?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了美国荣格派著名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师、畅销书作家詹姆斯•霍利斯的新作——《中年之路2:解开前半生的束缚》中第七章的部分精彩内容。本章内容结合了詹姆斯•霍利斯在诊疗中遇到的患者的真实案例进行分析,希望它们能给迷茫、焦虑的同学们新的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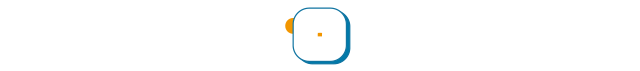
贯穿一切的焦虑
正当开写《中年之路2:解开前半生的束缚》中的第七章时,作者詹姆斯•霍利斯的女儿塔琳开始了每五分钟一次的宫缩。詹姆斯•霍利斯希望等到这章写完,就能见到女儿,还有他的第一个外孙女瑞秋。他期待着这双重的欢乐,但也要坦白一个神经质的想法。得知瑞秋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詹姆斯•霍利斯感受到的是焦虑,而非快乐。他的第一个念头——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自豪——又多了一个要操心的。他的第二个念头——关于塔琳:身为职业女性,她很快就要背上一副沉重的担子了。
他的第三个念头才是“正确的”那一个——对自然的伟大运转产生了深深的敬畏,我们是其中多么微不足道又多么重要的部分啊。在各式各样的灵魂中蕴含着一个共同因素。詹姆斯•霍利斯给自己得知女儿怀孕后的第一反应贴上了“神经质”的标签,这份焦虑他会自行解决,但他的反应显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条件反射,不受清醒意愿的控制。那么,面对如此奇妙又美好的事情,为何人会感受到一股暗流,好像被一下子拽到了阴郁的沼泽地?
马丁·海德格尔称我们这个种族是“向死而在"。索伦·克尔凯郭尔雄辩地阐释了“恐惧与颤栗”,还直接用它做了书名。奥登则称我们的时代为“焦虑年代”。
我们曾经连接着宇宙的心跳,一切要求都能被满足,却骤然跌落到这个危机四伏的地方。我们的降生就是创伤性的,它是心理上的创口,一个我们从未彻底从中恢复过来的灾难性事件。
人生中的绝大多数主题都是对这场灾难性的分离的回应。我们要么是想努力地回到与母亲脐带相连的状态,要么就是不得不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找联结。
既然不可能真的回到子宫,我们就会借助以下这些方式,与母亲建立退行性的认同:要么依然保有婴儿式的心态,要么借助药物和酒精来麻痹痛苦的意识,要么就是放弃自己的成长任务,把主权移交给某位上师或某种狂热的崇拜。
人人都有这种退行的趋势。然而,在我们向前发展的每一步中,日益增长的焦虑都如影相随。
事实上,每一天我们都得在焦虑与抑郁之间做出选择。
如果被退行的行为俘获,并因此破坏了个体化的进程,我们就要忍受抑郁之苦;如果战胜了心理上的懒惰,迈入外部世界,我们就要体验日益增长的焦虑感。这真可谓是左右为难。但是,无论有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确实每时每刻都要做出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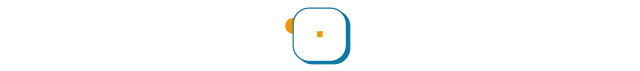
恐惧、狭义的焦虑、广义的焦虑
把恐惧、狭义的焦虑、广义的焦虑三者间的区别辨析清楚是很有用的。
恐惧是具体的。我们怕狗是因为之前被咬过。
狭义的焦虑是一种无来由的不适感,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引发它,某些具体事物甚至会让它持续一阵,但它通常是源自一个人对人生总体上的不安全感。人所处的环境、原生家庭、文化背景里的问题越多,无来由的焦虑就会越多。同样,创伤的性质也因人而异。
广义的焦虑则是人人都有的,它反映出人类脆弱的生存处境。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成“存在性焦虑”。
玛莎·杜鲁门·库珀在一首诗中描写了恐惧、狭义的焦虑与广义的焦虑是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混合交织在一起的,渐渐地,它们好像融合成了同一种感受:
假如说 你害怕的东西可以被抓起来 关在巴黎
那么你就有勇气去往世上任何一地
罗盘上一切方位都向你开放
除了指着巴黎的方向
你依然不敢涉足那座城市的边界线
你也不太愿意站在数英里外的山边
远远望着巴黎城的灯火 在夜色里渐次点燃
为确保安全起见 你决定
干脆远远躲开法国吧
可随即危险似乎逼近了国境线 你感觉到
心中那畏怯的部分 再次将整个世界铺满
你需要这样一位朋友
他知悉你的秘密 然后告诉你
先去巴黎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如果一个人曾经在巴黎遭遇过创伤体验,那么单是提到这个名字就足以唤起强烈的情绪。诗人借巴黎来比喻我们害怕的东西,对巴黎的恐惧渐渐泛滥,演变成了我们时时刻刻都背负着的焦虑,或者说一种非具体的恐惧。我们走到哪儿,巴黎就跟到哪儿;我们不敢确定是不是在某个地方就无意中踩上了它的边界线。条条大路通向的不是罗马,而是巴黎;那座城市也不再是光之城,而是“存在性焦虑”之城。即便避开了令我们恐惧的东西,巴黎也跟着我们;巴黎城无处不在。既然巴黎是躲不开的,要想削弱它对我们的暴虐统治,唯一有建设性的办法就是勇敢地面对它,去全然地感受它、穿越它。那位说出“先去巴黎”的“朋友”正是自性,我们内在的那个寻求疗愈的调节中心。库珀马上就知道,这是一片灵魂的沼泽地;他也知道,穿越这个阴郁之地的唯一路径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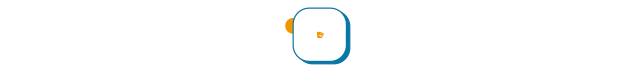
恐惧的背后,漂浮的焦虑
詹姆斯•霍利斯第一次遇上躯体化的神经症,是在精神分析研修期间。患者的名字叫莉莉,母亲情结把莉莉压得喘不过气。她母亲非常自恋,严重地入侵她的边界,成功地破坏了莉莉的每一段恋爱关系,好像要吞噬她的生活。在这种无意识的奴役状态下,莉莉一直非常抑郁和愤怒,却无法逃脱母亲那强有力的魔咒。她的左前臂会出现周期性的麻木。有一次在诊疗现场,在敞开内心的那个短暂刹那,莉莉暴露出心中被压抑的强烈愤怒,以及这种能量对她和她身边的人造成了多大的毒害。这让她感到极其焦虑。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狭义的焦虑与广义的焦虑之间的那条细线。狭义的焦虑源自一个极其有害的情结,而广义的焦虑则是每一个必须与父母分离的人都会体验到的矛盾情感。想要长大成熟,人就无可避免地要经历分离,这是有助于前进的;当人离开熟悉的环境走向未知,任何一种分离都会引发焦虑。恐惧症可能是被某种特定的创伤引发的。如果一个人曾经目睹过飞机失事,那他患上飞行恐惧症是很好理解的。但实际上,我们往往找不到与恐惧症直接相关的创伤体验。
在许多情况下,令我们恐惧的事物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代表,背后是漂浮在无意识中的、难以名状的焦虑。比如说广场恐惧症,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害怕去市场",从字面上看,这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病症。
然而,“市场”的特质就是开放,在那里有可能会与他人发生接触,它是不可预测的。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个人离开安全的家外出探索时,必须冒着“失去控制”的风险。
有一位女士,她的职业是银行职员,却有艺术家的天赋。她对高度有种特殊的恐惧。一连几个月,她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恐高症:她坐上电梯,逐步提高楼层,并走到观景窗前俯城市。
这种脱敏疗法确实有帮助,而与此同时,她看清了她的恐惧源自人人都有的焦虑——当我们面对脚下那辽远的旅程时产生的感受。她的恐惧症象征的是,如果自由地、肆意地去探索自己的天赋,她就会失去脚下的坚实大地。
因此,我们恐惧的东西或许是源于创伤,但它也常常象征着某种我们尚未意识到的深层焦虑,或是某些我们尚且不具备力量去承担的任务。讽刺的是,此类“恐惧"其实是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进一步深究起来,它或许是在对抗那种广义的、存在性的焦虑。
未被意识到的焦虑是最有害的,因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它会去哪儿,而它肯定要去往某个地方:要么投射出去,要么进入身体。
如今饮食失调很常见,特别是在年轻女性和中年女性的群体中。强迫思维不仅会令意识变得狭窄,还会迫使人采取行动去管理焦虑。因此,厌食症或暴食症把关注的焦点放到了身体形象与(或)食物上,这是因为这些东西似乎是能够掌控的。饮食失调不仅是意识范围变窄的问题,也是对焦虑的过度补偿。
另一名患者叫辛西娅,她在孩提时代就失去了双亲。一个不情愿的亲戚把她养大,管束、训诫她,却没有给她多少爱。青少年时期,辛西娅染上了盗窃癖,用偷来的东西替代不曾得到的爱。她也开始狂吃巧克力,然后再催吐。
来做诊疗时她已经成年,总是做掉牙齿的噩梦。牙齿象征着她的第一道防线。她还会梦见有敌人偷偷摸摸地潜入边境,可卫兵们在岗位上睡着了。
一方面,人生给她的只有酸涩,而通过暴食巧克力,她让自己品尝到甜蜜的滋味;另一方面,借助催吐,把那甜蜜的罪孽清理掉,她好似再度掌控住了那不胜负荷的焦虑感。
辛西娅遭遇的创伤是遗弃。没有一个人真正地爱她、支持她,这种体验引发了海量的焦虑。被遗弃在一个没有母亲的世界,这是无法承受的恐惧,所以她转而去担忧饮食问题。
当真正的恐惧就快浮出表面的时候,它很容易被激活,人会感受到恐慌的侵袭。这几乎是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感受,其他状态很难与之比肩,因为在恐慌发作的那段时间漫长得好像永无止境,人会感受到窒息、气短或心悸,这些都是彻底被压垮的感觉。
恐慌症发作时,去全然地、彻底地经历它(实际上,对待一切焦虑状态都应该这么做),这会迫使我们有意识地面对“灾难”,也就是说,正视那可怕的现实。
我们会发现,身为成年人,我们可以承受得住,甚至还能想办法去接纳它,有时还会有能力把它放下。“不放下”,意味着当我们下次再度偏离了狭窄小径的时候——我们会再次发现,我们又来到了无意识的密林。

就像小时候,我们总觉得有大鱼藏在床底下,或是有怪物藏在衣柜里,我们知道它就在那儿,它就要来抓住我们了。

用魔法思维安排生活
在焦虑状态下,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做出一些重复性的动作。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面临压力的时候,我们会有某些特定的、坐立不安的表现,比如会嘟哝口头禅、无意识地祈祷等等。这不仅是因为日常习惯会自行重复,也是因为我们经常会无意识地运用魔法思维来安排生活。魔法思维是孩童的以及所谓的原始文化的思维方式的典型特征,当我们处于退行和脆弱状态时,也会用这种方式想事情。借由魔法思维,我们让自己相信,我们的想法和行为会对世界造成特定的因果效应,正如世界也对我们有着秘密的因果效应一样。我们人人都会无意识地借助仪式化的行为来避开模糊朦胧的黑暗力量。如果仪式没能顺利进行,我们就会感受到更加强烈的焦虑。报纸没能按时送到,忘了某个东西没拿,或是不得不换一条新路线去上班……我们就会气急败坏。这些仪式就像有神力的护身符一样,是用来对抗海洋般浩瀚的存在性焦虑的手段,虽然它们脆弱得不堪一击,但我们还是牢牢地抓着不放。在典型的强迫症中,患者无意识地“选择”了重复性的想法和行为,将之用作一种仪式化的防御手段,来对抗那压倒性的、海量的焦虑。任何一种强迫思维或强迫行为都是在防御浩瀚的焦虑。偶尔有些时候,我们会主动选择神经症带来的“继发性获益”,换成委婉的说法,就是“生病也有好处”。

生病了,我们就可以扮演受苦受难的角色,或许就可以避开另一些令人倍感压力的要求,因此也就不必面对更大的焦虑。如果我身形肥胖,我或许就用不着面对亲密关系这个复杂又微妙的议题。通过对狭义焦虑的默许,我躲开了更为沉重的存在性焦虑。一切行为,即便是那些被我们称作“疯狂”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把它们视作对某种情绪的表达,或是对某种情绪的反应。无论症状伪装成什么模样,躲在何种象征背后,它表现出来的都是某种无意识的情感前提:我们变成了自己的创伤。我们不但深陷在自己的创伤中,同时还深陷在对创伤的反应中。


了解自我焦虑,走出人生危机
点击下图▼立即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