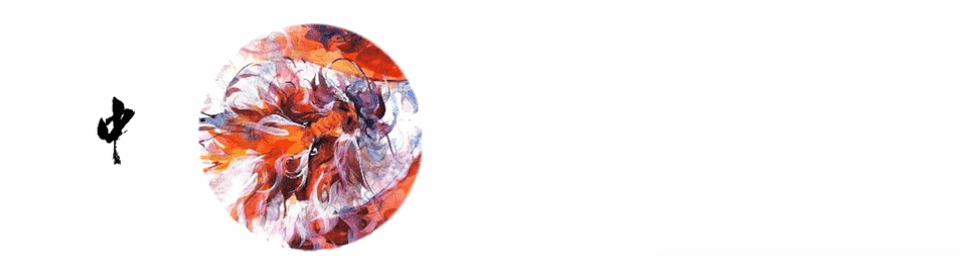

作者:张旭鹏
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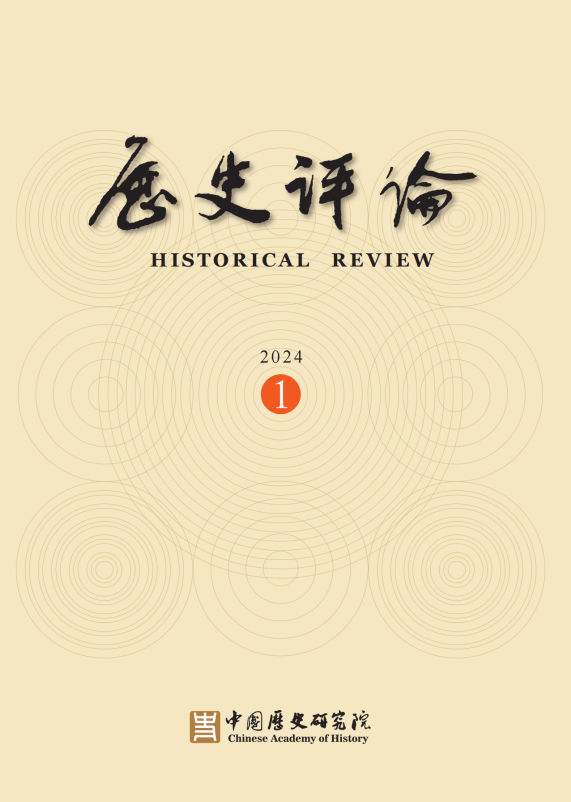
从外在表征看,历史上许多冲突似乎是“文明的冲突”,但冲突的真正本质并非文明本身。也就是说,文明冲突的原因不能归咎于文明之间的差异,而是作为政治体的国家之间对现实利益的争夺,这与同一文明内部不同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原因并无二致。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夏季号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称冷战结束后,文明之间的斗争将取代意识形态斗争,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冲突。1996年,亨廷顿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论证。亨廷顿直言:“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亨廷顿强调,西方文明将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战,他尤其担心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的对抗。
《文明的冲突?》的发表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出版,使得“文明冲突论”不胫而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影响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众多学科。“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就伴随着争议和批评。《文明的冲突?》发表后不久,《外交事务》就在当年的秋季号上刊登了包括三位非西方学者在内的七位学者撰写的回应文章,与亨廷顿商榷。这七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亨廷顿对文明作出了本质主义的理解,即文明在本质上不会发生变化,它固守着自己的核心价值;文明是排外的,冲突而非交融构成了文明关系的实质。第二,亨廷顿将文明与宗教挂钩,认为文明的核心是宗教,这完全忽视了现代社会中世俗主义力量以及文明国家日趋世俗化的现实。他将基督教世界依据不同教派划分为西方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拉美文明,却忽视了伊斯兰教内部类似的差异(比如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歧)这完全是一种站在西方角度看问题的先入之见。第三,世界上的许多冲突并非源自文明差异,而是现实国际政治使然。国家间最根本的冲突是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冲突,而非文明的冲突。中国学者也对“文明冲突论”进行了迅速回应。1994年,汤一介在《哲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了《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互相吸收融合而非对抗、儒家思想不是引起政治冲突和战争的因素、“文明冲突论”所体现出的“西方中心论”等三个层面对“文明冲突论”逐一予以批驳。1995年,王缉思主编了《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书,收录了28篇文章,分别从国际政治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对比、相互关系等角度对“文明冲突论”进行了评述。学者普遍认为,亨廷顿夸大了文明差异的作用,将之视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动因而不是众多动因之一。实际上,国家间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极为复杂的,文明的冲突只是一种表象,对现实利益的选择与争夺才是决定性的。在欧洲,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1998年出版了《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一书。米勒一针见血地指出,亨廷顿为了论证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合对抗西方的可怕前景,特别提到中国和朝鲜向伊斯兰国家出售武器的行为,却选择性地无视美国向伊斯兰国家出售武器的数量要远远高于中国和朝鲜的事实。按照亨廷顿的逻辑,如果中国向伊斯兰国家出售武器意味着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结盟,那么美国向伊斯兰国家出售武器是否就表明西方文明与伊斯兰世界的结盟?同样,伊朗在民用核技术方面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是俄罗斯,阿根廷与伊斯兰世界也有着广泛的核技术合作,难道这意味着东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或拉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结盟吗?因此,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完全经不起推敲。总的来说,学界对亨廷顿的批评,主要是认为他夸大了文明间对立,强调文明间冲突的一面,忽视了文明间交往、互鉴、合作甚至融合的巨大潜能。尽管亨廷顿辩称,“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想提醒人们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价值,避免可能发生的冲突。但亨廷顿将文明等同于宗教,以及对文明核心价值作出的“本质主义”解释,无助于理解文明之间差异和解决文明之间冲突。这一逻辑思维背后,其实还是预设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和“普世性”。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够知晓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日渐衰落的忧虑和担心。2004年,亨廷顿出版生前最后一部专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从移民的冲击、白人人口下降、多元文化主义的弊病等方面,论及美国国家特征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并表现出“一名爱国者”的关切之情。亨廷顿在书中坦言,随着拉美移民大量涌入以及在美国出生的拉美裔人口增多,美国极有可能产生分化:它拥有两种语言,即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文化,即盎格鲁—新教文化和拉美文化。亨廷顿担心,美国因为日益“拉美化”,将最终失去构成美利坚特性的重要因素:英语和新教价值观。为此,美国人应当坚守和重新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只要保持这一努力,即便盎格鲁—新教徒后裔在美国人口中只占少数,美国仍会长久保持其“美国”本质。《我们是谁?》一书虽然谈的是美国国内问题,但其立场和问题意识却与之前的“文明冲突论”一脉相承,不过更加忧虑和偏执。从亨廷顿的论调中不难看出,文明之间似乎只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甚至没有融合的可能。美国若要保持其“自由、团结、实力和繁荣”的领导地位,就必须让全体国民接受盎格鲁—新教文化,因为其他文明只会给西方文明带来“侵蚀”和“危害”。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中。文明的内涵也不是单一的和固定的,而是多元因素的有机融合。以现代西方文明为例,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而古希腊文明则深受埃及和西亚文明的影响。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发源于西亚巴勒斯坦的基督教逐渐传入欧洲,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另一个基础。中世纪晚期,欧洲借助伊斯兰文明对希腊古典文化的保存,才得以开启并完成对近代西方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文艺复兴。13世纪以后,随着蒙古汗国打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大量欧洲人开始进入亚洲,足迹直抵遥远的中国。这些欧洲人不仅深入接触亚洲文明,而且将亚洲知识引入欧洲,丰富和扩大了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拉赫在其皇皇巨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恰如其分地指出:“只有在大量的欧洲人开始去亚洲生活和工作,并开始将他们熟悉的欧洲文明的观念和实践,与他们在亚洲的见闻体会比较之后,欧洲文明的自我变革才有可能发生。”可以说,西方文明本身就是文明交流与互鉴的结果,它的发展壮大,更是在与亨廷顿所“担忧”的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的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完成的。从外在表征看,历史上许多冲突似乎是“文明的冲突”,但冲突的真正本质并不是文明本身。也就是说,文明冲突的原因不能归咎于文明之间的差异,而是作为政治体的国家之间对现实利益的争夺,这与同一文明内部不同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原因并无二致。公元前5世纪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通常被认为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也通常被认为是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分水岭。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正是由于希腊一方获胜,西方文明才得以摆脱被东方文明奴役的命运。实际上,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只不过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之战。所谓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对立的话语,只是后世欧洲人建构的政治修辞,在当时希腊的思想观念中并非主流。比如,以记载希波战争而垂诸史册的希罗多德,对交战的波斯一方并没有表现出文明上的傲慢和歧视,反而强调要平等地看待交战双方。他在《历史》开篇提到,他写作此书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对波斯人来说,这场战争的失败并没有给他们的文明带来毁灭性打击,更上升不到文明冲突的高度。同样,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也被视为一个具有文明冲突意味的重大事件,但其根本原因,实际上是源于宗教狂热、对东方财富的想象和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危机。否则,我们无法理解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为什么会针对同属基督教文明的拜占庭帝国。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原定攻打穆斯林控制的耶路撒冷,最终却攻占了同属基督教阵营的君士坦丁堡。图为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的作品《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描绘了君士坦丁堡当时的惨状 资料图片与之类似,当代国际社会所发生的看似文明间的冲突,究其本质,是国家间对现实利益争夺所致,是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致,既非文明自身的原因,更非文明背后所体现的不同价值观的原因。化解冲突的办法只有改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体现公正道义的国际新秩序。相比而言,中国古代很早便提出了“文明以止”的观念,强调对内“反求诸己”的道德自省与对外“和而不同”的包容原则。这一蕴含着深刻人文精神和理性智慧的文明观念,对创建一个和谐共处、美美与共的国际秩序大有助益。纵观历史,任何一种文明能够发展延续至今,都离不开对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流动性日益增强,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够保持其单一和固有的特点不变,也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脱离交往互动的世界而独善其身。对西方文明而言,大量穆斯林移民和其他非西方移民的到来,正在以多元文化和认同政治改变着西方文明特征。采用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移民政策,或者炮制“文明冲突论”的危机来施行强制同化,不仅不会保持西方文明的“纯粹性”,反而会加剧西方社会内部冲突。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文明而言,坚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才能持续发展,才能历久弥新。在国际层面,也只有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的价值内涵,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才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

